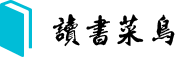《王氏之死》,[美]史景迁著,张祝馨译,南海出版公司,2024年9月出版。
内容简介:
清代郯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东小县,默默无闻,但多灾多难。妇人王氏,一个疑案记录中昙花一现的受害人,在飘雪纷纷的夜晚,惨死于丈夫之手。
利用县官回忆录、地方县志与《聊斋志异》,史景迁还原了17世纪末这个边缘县城的生存样貌:普通百姓挣扎于战乱、贫困和地方暴力中,没有官场人脉帮忙应对,也没有强大的宗族可以倚赖;无名女性没有法术和金钱做靠山,婚姻可能是毫无欢乐的陷阱,舆论与道德的纠缠随时将她们置于死地。
穿梭于聊斋的幻梦与郯城的苦难之间,他们在崩解的现实中,苦求肉身与道德的基本生存,在亦真亦幻的志怪故事中渴望正义的降临。这是一个有关幻想、肉欲与不安的故事,是对当时的郯城恰如其分的注解。在人鬼莫辨的世界,人们真切地体味着命运的尖厉。
作者简介:
耶鲁大学历史系斯特林讲席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代表作:《王氏之死》《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康熙》以及《利玛窦的记忆宫殿》等。曾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17)、古根海姆奖和麦克阿瑟奖。
目录:
1 致谢
3 序
9 第一章 观察者
35 第二章 土地
57 第三章 寡妇
71 第四章 争斗
89 第五章 私奔的女人
119 终曲 :审判
125 附录一 :《福惠全书》卷十四
133 附录二 :《郯城县志》卷九
139 注释
159 参考书目
编辑推荐:
1.史景迁经典代表作,复原十七世纪的县乡中国与家庭生活,再现动荡时代下小人物的命途祸福自明成化十七年,山东郯城,十事九灾:洪水、饥荒、地震、匪患与战乱无休止地循环。一桩私奔引发的疑案,揭开这个边缘小县的一角:县官黄六鸿在提振民心、催征赋税与打击黑恶势力中左支右绌、疲于奔命;百姓早已在连番的祸乱中变得麻木堕落。
2.一本基层县官的“职场指南”,围观一场地狱开局下的突围与破局,在重重困境中也看到挣扎的自己史景迁创造性发掘《福惠全书》,用一本基层县官求生手册,一览清初地方的众生百态:官场运作、钱谷刑名、户口徭役、财赋司法、里甲管理。在黄六鸿之前,已有四位知县因无法解决郯城逋赋严重情况及驿站废弛而遭革职。他与地主豪强斗智斗勇,与士绅富户迂回周旋,与黑恶贼众正面一战……黄六鸿的到来,照见每一个在天灾人祸中挣扎求生、寻求破局之路的小人物。
3.活在《县志》中的模范女性VS选择冲破命运围剿的王氏,一桩由私奔引发的疑案,召唤出只能在幻梦与现实的边缘实现的解脱《县志》中安放了五十六篇贞烈传记,鼓励已婚和未婚女性必要时可以死明志,为一个人鬼莫辨的世界增添一些道德抚慰。王氏,一个没能留下姓名的女人,从丈夫身边逃走,却又回来,在1672年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死于丈夫之手。一次反叛与出逃,换来一场在幻梦中实现的解脱。当付出一切却无所回馈时,每个郯城人都穿梭于聊斋的幻梦与郯城的苦难之间,他们在崩解的现实中,苦求肉身与道德的基本生存,在亦真亦幻的志怪故事中渴望正义的降临。
4.在《聊斋》的志怪故事中实现“自救”,在平行宇宙中触碰到真实的希望现实中他们沉默、麻木、被动地接受命运的摆布,而幻境里他们有仇有恨,有勇有谋,有法术,有金钱,对不公的世道勇敢反抗,对命运的伤害予以回击。官方记录无法窥探的底层人民的欲望、困境和道德的挣扎与不为人知的无奈,在蒲松林的笔下通过乡里传说和奇幻故事得以诉说。
5.新版归来,附送原始审案记录,再现史景迁灵感之源。在“蒙太奇”般的史料剪裁下,品味难以模仿的史景迁风格。
当时代的微尘穿过郯城,一粒一粒压到王氏的身上时,这个故事没有问题与答案,只有真实的“人”的温度。史景迁通过“蒙太奇”般的剪裁手法,在历史浪潮中拾起小人物的鲜活生命,召唤边缘百姓几乎被人遗忘的真实生活。
精彩书评:
“一本令人难忘的历史重现之书。”——《新共和周刊》
“一个连名字都没能传下来的寻常农妇的死亡,成了史景迁笔下动人心魄的史诗。他以穿透岁月的观察和惊人的叙事力,把那个灾荒、瘟疫、匪患与重税盘剥循环往复的世界拉到我们面前。真是一个关于学术研究与历史写作的经典示范。”——罗新“不管它被归于虚构还是历史重构,都是文体和叙事上的杰作。”——哈罗德·布罗姆
在线试读:
我对王氏的反应模糊而深远。于我而言,她就像是退潮时海水中一块闪闪发光的石头,我几乎是怀着遗憾的心情从浪涛中将它拾起,心知随着阳光蒸干水分,石头上的色彩也会逐渐褪去、消失。但这块石头的色彩与纹理并未消散,反而在我手中变得更加鲜明。我时不时还能感受到,这块石头正在向握持着它的血肉传递温度。历经几个世纪,中国对农村的苦难已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写法;类似上述引文可见于众多方志与官员回忆录,通常只是堆砌辞藻,缺乏实质。但至少对郯城而言,此段描绘是切实可感的。兖州府下辖二十七县,以郯城与沂州最为贫困。黄六鸿比较二者时,发现郯城的境况显然更为严峻。明末,县内设有八座应急谷仓,分别位于县内四个乡、马头镇、南部驿站、县城及西北的神山。至1670年,八座谷仓已悉数被毁。1668年大地震毁坏了县里的诸多屋舍楼阁及大片城墙,但即便在此之前,多处建筑也早已沦为废墟。县医馆消失无踪,南往宿迁的通衢大道上方的桥梁也已倾圮,各座寺庙亦被毁坏殆尽。
16世纪末以降,中国各地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将许多旧有的力役与兵役改纳银钱。及至1670年,郯城百姓大多已改为以银钱纳税,然而仍有几种徭役未能蠲免:例如收集大量柳驻地;护送装运物资的骡队;以及向工部提供兴建宫殿所需的特种木材—这些木材必须运至一千六百七十里外的北京。此外,尽管郯城县因穷困,且远离主要水道,郯城工人通常无须在黄河与大运河上服役,但因南方骆马湖的大规模疏浚及筑堤工程,此项豁免在17世纪50年代初期、1666年及1670年都曾被收回。
在郯城,也能找到寡妇不时为财务压力所苦的证据,虽然常常被改嫁的压力所掩饰。寡妇吴氏需要独自抚养一岁大的幼儿,《县志》中有一段简短的传记,其中有云:“姑卒,夫兄逼令改嫁。氏剪发毁面,尽归故产于夫兄。携孤祉依母以居。”寡妇安氏之死则有以下描述:“妻于归甫半载,羡婴暴疾而亡。氏恸哭,誓欲同死,乡人未之信也。次日,将己妆奁衣服焚之,舅姑不能禁。宗党聚而观焉。氏抚膺长叹曰:‘夫乎!吾从尔逝矣!’即以身跳入火中,邻妇救之出。守者始密。又次日,氏谩姑出,即扃门缢于房中。时年一十九岁,人称烈妇云!”
冯可参以最高标准甄选并撰写《郯城县志》中的“人物志”,针对女性尤其如此。“贞烈”妇女传的传播,是地方名士将其认为正确的女性举止强加于他人的重要方式之一,此举也与当时朝廷力推的价值观完全一致。所谓女性的行为举止,一般即指女性对丈夫的行为。列载的女性中,有十五人自杀,其中十三人是出于对亡夫之忠贞,或为免遭强暴,令夫妻二人蒙羞。与为复仇或因愤怒而自尽者不同(黄六鸿对此类行径多有批评),若是没有子嗣的孀妇自杀,则会在道德上被视为“正确”之举,因为此举显示出女性对丈夫的崇敬。即便丈夫在地方上名声不佳,其遗孀自尽亦会受人褒赞。这从高氏之案中可见一斑。高氏之夫因谋杀罪被羁押于郯城狱中,妇人前去探视病重的丈夫,在牢中企图用裹脚布缢死自己与丈夫。狱卒出手制止,并不许她再次探望,她只得前往城隍庙,向城隍自白“:妇人从一而终,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奈何独生?妾志定矣。与其身殉于终,孰若断之于始。妾之事,惟神鉴之。”随后便在城隍庙廊下自缢。此类自杀并不限于受过理学忠孝思想熏陶的士大夫家庭。例如,在丈夫病逝后自尽的刘氏,本人为木匠之女,其夫为佣工;另有一位自尽的孀妇,其亡夫为小商贩,往来于李家庄和莱芜镇两地做买卖。
郯城依然飘雪纷纷。任某扶起妻子的尸身,用她的蓝夹衫裹住她的肩膀。他打开家门,背着她穿过树林,朝邻居高家走去。他的企图如下:王氏死后,他携尸身至高家门前,称其与高某素来有私情,为高某所杀。此番说词似乎合情合理:王氏曾与人私奔,而高某又为人暴戾。二人可趁任某外出务农时,每日里在一起卿卿我我。但任某终究没能带王氏走到高家。当他行至幽暗林中,犬吠声起,躲在高家门楼下休息的更夫鸣锣示警,高家点亮了一盏灯火。任某将尸体弃于雪中静候。无人前来探查。灯火熄灭,四周再度归为寂静。他将王氏留在原地,独自返回空宅,锁门入睡。王氏的尸身整夜横卧雪地中。及至被寻获时,样貌仿若生者:严寒竟令其脸颊上保有些许鲜活的血色。王氏已死,但她身后之事或许比生前的问题更难解。生前,除了以言行伤害公公与丈夫或与其私奔的男人外,王氏大概并无力量伤害他人。但在她死后,其怨念充满了力量与危险:身为饿鬼,她可在村中游荡数代之久,难以安抚,也无法驱除。三十年前,年轻的寡妇田氏曾威胁,若不能如愿独自过活便自杀,变成厉鬼追索徐家,结果她如愿以偿。如今田氏仍安然无恙,足以说明郯城人极为重视此类言论。黄六鸿认为,应用一副好棺木将王氏安葬在她家附近,“以慰幽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