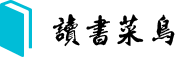《思想的假死》,[德]彼得·斯洛特戴克著,常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
内容简介:
在广受赞誉的《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一书中,彼德·斯洛特戴克将“实践”视为决定性的“人类境况”。而在本书中,他分析了这种有关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新视角,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理论工作者与科学工作者看待其学科的方式和他们的工作内容。彼德·斯洛特戴克将理论和科学理解为一种通过生成的练习而唤醒工作者投入生活的方式。
本书的叙述涵盖了两干多年的哲学发展历程。它始于柏拉图对他的老师的描述——那位老师因沉思而伫立在原地一动不动——继而涉及胡塞尔、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思想。最初的雅典学院是一个练习的地点,在那里人们学习如何从世界中抽离。胡塞尔的现象学劝导人们从存在执态中后退一步,练习不参与。斯洛特戴克呼吁人们思考“悬置的人”如何保持创造性。
作者简介:
彼德·斯洛特戴克,当代德国哲学家、文化理论家,卡尔斯鲁厄艺术与设计大学哲学和媒体理论教授。曾于2002年至2012年担任德国电视节目《哲学四重奏》的主持人。斯洛特戴克常自称是时代的诊断者,对社会现实进行分析评判,力求把握未知的未来,找到有利于现实的良方。他的代表作包括《玩世理性批判》《资本的内部》《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球面学》三部曲”等。他曾获欧洲政治文化奖和赫尔穆特·普莱斯纳奖。
译者:常晅,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师,博士。译有《资本的内部》《购买时间》《海德格尔与妻书》《魏玛共和国的兴亡》等著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1项。
目录:
序言 作为实践生活形式的理论
I 理论与苦修主义,现代与古典时代
II 观察者出现了:论有悬置能力的人的产生
III 理论的假死及其变形
IV 认知的现代性:刺杀中立观察者
编辑推荐: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彼德·斯洛特戴克引经据典,从古希腊开始回顾哲学发展的历程,探索哲学与哲学家身份的演变,总结思考的本质。他挑战了人们对“思考者”身份的传统看法,是一本兼具历史视野和批判深度的哲学著作。
在《思想的假死》中,斯洛特戴克深入探讨了哲学家如何通过“假死”状态进行思维的重构,摆脱日常生活的束缚,进入一种纯粹的思考模式。他的观点启发读者重新审视思维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哲学如何在社会变迁中保持其独立性。
斯洛特戴克也揭示了在一步步的演变中,思考者脱离实际的倾向,学院逐渐成为象牙塔,失败者的浪漫主义逐渐蔓延。他提醒人们反思,提倡在实践中思考。
精彩书评:
知识追求如何变得不切实际?在这篇充满激情的演讲中,斯洛特戴克试图为我们解释一个看似理所当然的观点:理论思考与从生活中抽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问题始于柏拉图对苏格拉底之死的描述,即苏格拉底之死是其哲学实践的逻辑终点。此后,尽管偶尔会有像尼采这样的英雄式异见者,但理想中的思想家主要是一种“假死的人”。 斯洛特戴克以辛辣的笔调讽刺“失败的浪漫主义”或知识分子的“承诺”。他大胆地断言,我们所谓的“文化”,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一种非化学的“镇静剂”。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追求一种既不纯粹主动参与也不纯粹沉思的生活,斯洛特戴克称之为“实践生活”。 ——《卫报》
在线试读:
(“序言 作为实践生活形式的理论”)
我意识到,这种思考把我带入了一个目前少有人进入,且更少有人研究的领域。现在有谁会质疑,为什么保护杰出的假死者对于古代欧洲的理论文化来说,就像圣人崇拜对于中世纪教会一样重要?正如我们离从“上帝已死”这句话中得出所有的结论还有一段距离一样,我们离理解“纯粹的观察者已死”这句话的所有隐含含义也非常遥远。认知过程的世俗化所需要的时间显然更长,如果我们把它和19世纪的大多数实证主义者、20世纪的核物理学家或的神经科学家所能预见的东西相比的话。杀死神圣的怪物——直到最近才被视为认知者的方式——这只是一个开始,结果如何仍然未知。此外,由于相当多的行动者联合起来参与这件事——我将总共列举出10个之多——他们有着广泛的动机,使用的工具种类繁多,所以实际上也就不可能将责任按照确切的份额分配到每个攻击者的头上。
从事实上讲,这起犯罪涉及必须被称为“天使谋杀”(Angelozid)的案件,也就是说涉及一个从未被正式追诉的案件,因为无论是公诉人还是认识论者都不承认天使的存在。他们不认为天使是一类可被谋杀的对象,当然也就不可能追究针对他们的罪行。天使谋杀案的案例分析很复杂的原因在于,无法用证据来证实犯罪事实存在。虽然有大量的动机和疑似凶手,但没有天使样貌的存在。相反,在实践理论的天使被破产清算的地方,真实的、过于真实的人,留在了报告厅、实验室、图书馆和永远开不完的系讨论会上。是的,如果这些去天使化的受害者真的有什么可抱怨的,那就是他们从优选的非现实性被拉回到了世俗的存在中。并非所有复活的对象都欢迎他们回归全然的生活;然后,我对一些当代理论家持怀疑态度,因为他对从无趣状态的美丽死亡被拖回认知的现实政治的舞台而感到遗憾。在此,我也请大家耐心等待,直到我的论述发展到足以让我来具体化我所能表达的东西。
似乎还有必要做出一个初步的。因为只有当我们认真对待“实践”一词的所有含义(包括作为练习或训练)时,下面的一切内容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适当的分类,所以我必须事先对人类实践做出。它一直以来被现代主义理论所忽视,甚至成了一个被肆意地推到一边和蔑视的概念范畴。我的新书《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论人类学技术》在刚刚出版后的几个月内得到了非常多有建设性的建议。书中,我试图恢复实践的崇高地位。鉴于实践在高度文明的精神气质中的重要性,这一点其实早就应该实现的。然而,由于现代哲学概念中的系统性缺失和主流社会学行动理论视野中的盲点,它至今仍被否定。在《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中,我比较详细地展示了传统的人类行动的分类,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最初只用于僧侣的“积极生活”(vita activa)和“沉思生活”(vita contemtiva)之间的区分,是如何与使实践这个维度不可见,甚至实际上不可想象的效应联系在一起的。一旦我们接受了“积极”和“沉思”之间根深蒂固的区别,好像它们是完全排他的,对于彼此是彻底的替代选择,那么,我们就会忽视人类的行为其实是一个范围很广的复合体,它既不只是积极的,也不只是沉思的。我把这称为实践的生活。
从本质上讲,实践的生活构成了一个混合的领域:它似乎是沉思的,但又不放弃积极的特征;它是活跃的,但又不失沉思的视角。实践,或曰练习、锻炼,是最古老的,最有效果自我参照训练形式。它的影响并不像劳动或生产的过程那样涉及外部状态或对象;它们发展了实践者本身,使他作为能动的主体“塑造形态”。练习的结果显示在当前的“状态”中,即练习者的能力状态。根据不同的场合,这些能力状态分别被称为体质、美德、技艺、能力、卓越或健硕。作为其训练序列载体的主体通过完成典型的练习来保证和提高自己的技能——同一难度的练习则一般被认为是维持性练习,而难度等级不断提升的练习则是一种发展性练习。恰好古希腊运动员把他们的训练称为经典的“苦修”(askesis)(早期基督教僧侣也自命为“基督运动员”,这成为一种划时代的、持续施加影响力的模式),它总是同时包含着两方面。当我们把练习强行区分为理论和实践或积极和沉思的生活时,我们就忽略了其固有的价值。这同样适用于当代作者在行动理论中引入的区别,例如,把交流型行动和工具型行动,甚至把工作和互动放在一起做比较。这种对实践领域的结构划分也让实践生活的维度不可见。
我的书试图对实践生活的延展、权重及其大量的形式给出一个印象。书中,我引用了尼采的一句令人回味的话语:从宇宙中看去,形而上学时代的地球必然看起来像个“苦行僧星”——在这颗星上,没有生活乐趣的苦行僧民族对抗其内心本性的斗争是“最持久和最普遍的事实”。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抛弃否定生命的苦行主义,再次获得已经过时太久的肯定生活的技艺。
尼采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矛盾的效果:关于地球上的居民“对自己”做出的所有工作,他们的禁欲苦修、他们的训练和他们为塑身所做的努力,无论这种趋势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现代社会哲学家、批判理论家和无处不在的社会心理学家对此还是一如既往地不了解,因为他们对这种现象仍然戴着一副致盲的眼镜。在汉娜·阿伦特广为流传的《人的境况》(Vita activa)一书中,实践生活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它在书中也并没有出现——这对于一部承诺解释“人类状况”(human condition)的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结果。现代生活世界中的公民早就知道了这一点,他们没有受理论家们的获得性盲目所影响。他们已经打开了被官方忽视的训练实践的通道,尼采提出的提升式苦修现在被冠以不同的名头——进修、训练、健美、运动、节食、自我设计、治疗、冥想——这些已经成为西方肯定绩效的亚文化中的主导方式。此外,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东亚古老而伟大的实践大国,即中国和印度(就像曾经经历过的进程一样),已经完成了向全球导向的训练形式的转变。他们已经启动了一个全新的、积极的绩效制度,很快可能会超过厌倦了的欧洲人所完成的一切。
在关注人类生存的实践方面时,我考虑到了一个表面上微不足道,其影响却不可预测地深远的事实:人们所做的和能做的一切,都会被掌握得好一些或者差一些,相应地,做的也会有更好些的或更差些的。总是有技艺精湛者和实践操作者不断地参与到自发形成的关于技能和操作的或好或坏的排序中来——我把这类区分行为定义为人类生存中固有的纵向张力的表达。我所提出的实践的技术定义,为非自愿的垂直性现象开辟了第一种进入方式:在每一次实践的行为中,行动都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执行的,即它现在的执行共同制约了它以后的一系列执行。我们可以说,所有的生命都是杂技,尽管我们生命表达中只有最小的一部分能够以其一直以来就是什么的样子而为我们所感知——那便是实践和生活方式要素造成的结果而那生活方式行于几乎不可能的钢丝上。
在《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中,我开始关注与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说的“轴心时代”(Achsenzeit)所出现的激进伦理有关的古代实践体系。这是公元前的一千年内通过帝国的(和帝国批判的)世界面貌创造而来的文明大事件。在我看来,古代的训练文化主要是伦理上的自我改造系统。它们的功能是使人类与宇宙的总纲领或神圣的教规保持一致。他们经常规定过度的身体和精神禁欲主义。在欧洲的现代,有一种趋势是将这些体系统统纳入“”这个具有误导性的标题之下,而没有考虑到“”作为一个基督教罗马的概念——虽然在启蒙运动中被中性地用作一个文化人类学类术语——被强行移植到了这些现象上。这个词很难对印度、中国、伊朗、犹太和古代欧洲的生活哲学体系做出公正的评价。我们在下文中不会再讨论伦理实践综合体和屈从于更高权力的“性”实践以及培养幻想的集体仪式形式之间的区别。目前,我们关注的唯一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将我们对古代伦理学中所揭示的隐性和显性实践生活结构的洞见扩大到理论行为领域。如果我不能确定一个肯定的答案,我将不得不在这一点上中断我的考察。
顺便提一下,我在《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一书中也提议将艺术史学科重新表述为艺术的或 精湛技艺的禁欲苦修的历史时,将实践概念包含的区域做了类比延伸。就像科学史通常假定从事其各自学科研究活动的科学家已经存在一样,艺术史自始也假定作为艺术品生产者的艺术家是艺术活动的天然载体,而且这些行动者一直存在。如果我们把这两种情况下的“概念舞台”旋转九十度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我们首先观察的是艺术家成为艺术家的努力,又会发生什么?这样我们就可以或多或少地从一个侧面看到这个领域的每一个现象,除了我们熟悉的作为已完成的作品的艺术品构成的艺术史之外,我们还可以获得一部使艺术成为可能的训练史和塑造艺术家的禁欲苦修的历史。用一个类似的手法,在通常的作为问题、论述和结果的科学史旁边,我们同样可以追踪使学术得以进行的实践和练习是如何形成的——从而叙述一个自我征服的历史,使那些迄今为止使用理论前阶段的“正常语言”的人进入理论思想的联盟中。这种类型的间离感是禁欲苦修史研究任务的特点。
这会导致我们的观察方式有哪些变化呢?我在关于我卡尔斯鲁厄的同事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的《图像与崇拜》(Bild und Kult,1990)一书的中,对此做出了阐释。这部关于“前艺术阶段”图像的精湛历史,在我看来在创造图像的禁欲苦修的历史这方面是最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像贝尔廷所说的那样,假设欧洲绘画文化的传统是从希腊化的基督教崇拜的圣像画开始的,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一种图像制作的实践形式,其中艺术和苦修实践形成了一种完美的统一体。圣像画家一生都在无休止地重复工作,处理由少数元素组成的单一创作对象,他甚至相信自己只不过是超自然的图像之光的工具,而这种图像之光假借他的手涌入作品。这始终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即真实的原始画面即使没有画师作为中介也能投射到视觉世界中,尽管这种情况极为罕见。这种直接的倾泻将是一个神迹的幻灯,无须借助画家的通道,直接从天堂降临。至于用人手绘制的图像,只有在它们忘我地与未绘制的原始图像相似时才是好的。基督就是这样一张幻灯片,是三维的,能够受苦;他在维罗尼卡面纱上的形象也是一张幻灯片,但投射在二维空间,没有受苦。从“”圣像的绘画练习开始,我们可以将欧洲艺术史描述为技能练习的大量积累、形式上的卓越和技术上的苦修,最终在诞生了那些著名的最高形式。这个过程为艺术方法的稳步扩展以及对艺术家重要性的夸张想法创造了条件。艺术卓越的自我指涉性不断增加,直到现端的分水岭,导致了视觉艺术中实践意识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