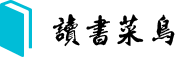《以爱为名的支配》,[日]田岛阳子著,吕灵芝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国文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
内容简介:
日本女性主义传奇人物田岛阳子代表作品初次引进。渴望被爱的心理,是女性一生的陷阱。作者从亲身经历出发,讲述了在“亲缘压迫”下成长为“女性主义者”的思想历程。本书探讨了所有东亚女性都深有共鸣的生存问题,大胆揭露了原生家庭、婚恋、工作、育儿等领域的结构性歧视。本书回答了“女性为什么这么难活?如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今后如何奋斗?”等问题。评论家认为本书是日本女性主义入的zui佳入门,亦是当代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要读物。
作者简介:
田岛阳子,1941年出生。英文学及女性学研究者、原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前日本参议院议员。活跃于20世纪90年代的著名女性主义者。从1991年到2003年出版了10部女性主义论著,在日本女性心目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她在为女性发声的舞台上活跃至今,参与了众多电视节目(如《北野武的电视擒抱》)、广播、杂志、纪录片、电影、戏剧和广告,不仅是日本当代重要的女性主义思想启蒙者,还影响了同时代的上野千鹤子等女性学者。《以爱为名的支配》是田岛阳子颇具影响力的著作。
目录:
第一章 觉醒之后已是女性主义者
寄人篱下的屈辱是我的生存原点003
忍受责罚的是“反应迟钝的孩子”005
无法逃离讨厌的事物的“奴性”007
卧床不起的母亲用二尺长的尺子责罚我009
压抑的轮回,造就了家庭版“霸凌结构”012
讨人喜欢的人,都为了迎合而扼杀“自我”016
无法逃离霸凌者的心理019
一边洗碗,一边因身为女性而流泪的母亲022
女人只有枷锁之下的自由025
第二章 女人被规训成了奴隶
“妖怪”支撑“绅士”的所谓国际化城市031
男女关系造就的“城市中的农村”035
女人只要被养着就得不到男人的尊重038
男人为奴采棉花,女人为奴生孩子042
桨帆船底层的划桨奴045
防止女人逃走的肉体、精神、社会束缚048
婚姻是女性家务劳动无偿化的制度050
不愿容忍免费家务劳动的“个性”女人登场053
“母性”是男性社会唯一认可的女性权利056
女人和男人的关系仍停留在奴隶社会059
第三章 变成小小的女人吧
“男人气质”是独立,“女人气质”是为男人付出一切065
“大男人”和“小女人”造就的悲剧069
社会与家庭让女性生来便受到“女人气质”的养育072
在束缚中成为小小的女人077
昭示女性身份、束缚女性自由的服装079
为何强制初中女生穿制服短裙083
定义了女性审美和服装的男性凝视086
改变被规训的审美,脱离歧视文化090
成为玛丽亚或夏娃,还是成为一个人093
第四章 逃离菲勒斯中心主义
侵入式的性爱是对女性身体的粗暴占领099
男性本位的性爱与成为附庸的女性102
非侵入式的爱105
为融入男性社会而讨要爱的女人108
失去自我的女人成为性别歧视的帮凶111
规训女人爱慕男人的男性社会116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最符合现代日本的男女关系121
查泰莱夫人的存在就是为了生产继承人125
由生命的共鸣而生的性爱128
男性能够超越菲勒斯中心主义吗131
无性现象是希望从阳具崇拜中得到解放133
第五章 如何斩断家庭的压抑轮回
男性代理人(家庭主妇)创造的家庭版军队组织139
管教是以爱为名的霸凌145
上到极限的压抑发条因恋爱而松弛147
名为恋爱的爱憎代理战争150
独立男女之间纯粹的力量对决154
压抑的核心是直刺对方要害的支配力量158
四十六岁那年总算切断的母亲的咒缚161
为了超越自身的不幸模式而进行的治疗164
与自我对话,接纳自我,在自我中发现神性167
我深爱着只能活在那个时代的母亲170
将自己从压抑中解放的我的“女性主义”174
斩断压抑,为自我而战177
第六章 寻求纯粹的女性主义
性别分工与生态资源183
控制欲强的父母造就的“不孝子女”187
没有自我的“贤妻良母”190
亲手赚钱乃是自立之本194
只要困于“母性”,女人就永无自由197
活在“树形人生”中,恋爱、婚姻和生育都是分枝200
但凡男人有为女人让道的度量203
被迫脱离“有毒男性气质”却得到自由的男人208
调整女人与男人之间的时间差211
与自食其力、充满魅力的女性欣然相遇214
无须戴冠的女性主义219
即使拒绝社会劳动,家庭主妇也是资本主义的帮凶224
关键不是谁来支付家务劳动,而是男女个体如何改变227
今后需要“追求平等的心灵”和“现代化的双脚”230
女性主义的目的是探索有民主而无歧视的富饶社会234
后记太郎次郎社版本237
后记讲谈社 α文库版240
给我们带来幸福的女性主义250
编辑推荐:
1.日本女性主义传奇人物田岛阳子,代表作首次中文引进!
田岛阳子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主义者之一,也是传奇无数的事业型大女主:一路逆袭成为法政大学教授,事业横跨文娱政三界……时年83岁的她在为女性发声的舞台上活跃至今。上野千鹤子赞道:“女性主义者的代名词就是田岛阳子!”
2.以真实经历写就,一个“东亚女儿”的逃离、觉醒、自由之路。
田岛阳子在《以爱为名的支配》中,从亲身经历出发,讲述了在“亲缘压迫”下成长为“女性主义者”的思想历程。
3.大胆揭露专门针对女性设下的隐形陷阱,所有女性成长路上的避雷指南。本书探讨了所有东亚女性都深有共鸣的问题,大胆揭露了原生家庭、婚恋、工作、育儿等领域的隐形歧视结构。本书回答了“女性为什么这么难活?如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今后如何奋斗?”等问题。
4.毒舌吐槽,戳中爽点,精神状态超前的嘴替金句!
·男性文明把工作分给了男人,把爱分给了女人。
·女性在家中从事的那些难以察觉的琐碎劳动,有着普通男性月薪无法承担的价值。可以说,女性才是家中的顶梁柱。
·女性做不好工作,所以女人不行;女人工作做得如鱼得水,又会被说“一点女人味都没有”。不管选哪个,都得不到认可。这被称作双重束缚。
精彩书评:
读了一大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不愧上野的老师,行文风格更干脆,更有力量。
——豆瓣读者
全书围绕“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和压迫”这一主题,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切入点,娓娓道来,没有一丁点晦涩难懂的学术理论。鼓励女性拿起思想武器冲破牢笼,勇敢去做一个人,而不是去做一个被男权社会所定义的女人。
——豆瓣读者
第六章对“戴冠女性主义”的批判性解读对我还蛮有启发的,可能我们在系统化、理论化女性主义的过程中,确实容易影响到视角的纯粹性,也让目标变得过于宏大而不够清晰,这点和贝尔·胡克斯的看法也是有相同之处的。全书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这里最优先的是“我”,而不是女性主义;不是“我”贯彻女性主义,而是女性主义对“我”有用,所以我用了它。我自己的女性主义观与其非常相似:1.优先做自己喜欢的事;2.尽量不对其他女性的选择指手画脚。
——豆瓣读者
前言:
前言
只要一提起女性主义,经常会得到这样的反应——“丑女多作怪”“没少被男的欺负吧”。
我的女性主义原点,是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十分严厉,即使她在因病卧床、无法起身的那几年,也常用二尺长的尺子责罚我。她一边吼我“好好学习”,一边骂我“光会学习有什么用,没点女人味,以后嫁都嫁不出去”。我的整个童年,都被母亲这样的话语紧紧束缚着。
我十八岁辞别父母来到东京,依旧被母亲看不见的丝线支配着。身为女人的不自由使我无法畅所欲言,无法做真实的自己。我为什么如此痛苦?为什么活得如此艰难?一定是我不够成熟。这使我痛苦万分。
我想摆脱痛苦,便努力思考、反复分析了我与母亲、我与男性、我与社会的关系。当我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给我自己以及全体女性所处的被歧视状况做定性分析时,我得到了救赎。为此,我花了漫长的时间。
我得以知晓,那个让我痛苦不堪的母亲,也因她的母亲而痛苦不堪。母亲和她的母亲都因为身为女性而无法过上自己想要的人生。母亲们只能通过支配自己的女儿来发泄生活中的郁愤。我没有错,母亲也没有错。
当我看见束缚女性的压抑轮回之时,我原谅了母亲,也为此前一直困惑不解的问题——女人为什么这样—找到了自己能够接受的答案。
本书讲述了我与对我影响巨大的母亲之间的纠葛,以及我在解放自己的过程中的发现。折磨女性的究竟是什么?分析其根源,我得出结论,那是支配着每一个女性的“结构性女性歧视”。
知识会带来痛苦。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了歧视。然而受到歧视的人即使想逃,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处什么样的状况,因此逃无可逃,这样更痛苦。首先,要知道自己的处境,我认为这才是救赎的第一步。
田岛阳子
二〇〇五年十月
在线试读:
第一章 觉醒之后已是女性主义者
1寄人篱下的屈辱是我的生存原点
我出生于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年份。在我四岁那年,战争结束了。母亲当时是个普普通通的已婚妇女,没有一技之长,所以我们不得不靠着亲戚糊口。我和母亲就这样在疏散之地体验到了寄人篱下的屈辱。
住在父亲老家时,有一个令我毕生难忘的经历。我们跟许多亲戚住在一起,吃饭时每个人面前都有鱼,只有寄人篱下的我和母亲没有。当时我年幼不懂事,对母亲说:“妈妈,我也要鱼。”母亲则说:“闭嘴吃饭!”一巴掌打得我不敢抱怨了。类似的用餐事件,发生过好几次。
用餐歧视真的让人非常难受。母亲自己其实也很不甘心,后来对我提起过无数次。我觉得,那起“吃鱼事件”深深烙印在了我的性格之中。
人在两三岁时体验到的不得不向别人乞食、不得不寄人篱下的生活,是一种毕生难忘的屈辱。这种屈辱成了我人生的一个原点。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即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能无须顾虑任何人,敞开肚子吃自己爱吃的东西。我想,正是这个愿望使我后来衍生出了自己赚钱的想法。
2忍受责罚的是“反应迟钝的孩子”
疏散到母亲老家后,还有一个令我毕生难忘的经历。
当时正值战争中后期,各地都在频繁举办葬礼。因为总在“焚化场”附近见到和尚,我们这些小孩就学会了模仿和尚玩葬礼游戏。我跟同岁的表妹正子拿了姥姥的腰卷1斜挎在身上,嘴里念着“南无妙法莲华经”满村子走。可以想象,很快就有人找到大人告状,说我们不成体统,穿着腰卷学和尚岂有此理。我们两个人都被狠狠骂了一顿,还要遭受艾灸惩罚。
那时,表妹正子可能因为有经验,大人一点着火,她就飞快地拍掉身上的艾草跑了。姥姥和我的母亲竟然高兴地夸奖了正子。
她们说:“正子好灵巧啊!”
但我觉得自己在遭受责罚,必须咬牙忍耐。然而强忍着艾灸的滚烫的我,却听大人骂道:“你真是反应迟钝。”她们拿我跟正子做比较,然后说:“这孩子就是个傻大个,反应太迟钝了。”于是,这就成了姥姥和母亲对我的固定印象。
我很想辩解:“大人说要艾灸,我觉得应该听话,所以一直忍着。”可是三四岁的孩子说不出那样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正子不听话反而被夸了,而我努力忍耐却要被笑话。当时的不甘心,现在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3无法逃离讨厌的事物的“奴性”
时至今日,我已经非常明白艾灸一事的内涵了。它意味着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就被植入了“奴性”。正子这种没有在城市生活过,一直在乡间自由玩耍的孩子,能够更敏锐地察觉到逼近自己的危险,就算那是大人的责罚,她也能发挥出拒绝自身受到伤害的力量。
当时农村人都很忙,根本顾不上管教孩子。所以至少可以说,正子还没有受到与我同等的压抑,也没有被植入“奴性”。
母亲是个性子暴烈、心理洁癖严重的人,想必在我三岁之前已经用各种手段规训了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因此,我在那个时候很自然地放弃了抵抗,觉得妈妈说的话都要听。艾灸明明是对幼儿的虐待,但我还是认为应该听妈妈的话,只要听话就能得到夸奖。也就是说,我在年仅三岁时,已经被植入了那种性格。
每次妈妈打我,说:“这都是为了你好。”我都乖乖地撅起屁股说:“妈妈我错了,我是坏孩子,你打我吧。”我做不到像正子那样拔腿就跑。我想,这就是“奴性”的萌芽。
无法逃离疼痛,无法逃离痛苦的状况。一旦陷入痛苦的状况,就容易想象这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够好,一味地责备自己。这种心理倾向正是在那种管教中形成的。我一心以为,只要当好孩子就能得到爱,只要当好孩子那个人就会对我笑,会拥抱我,会给我做好吃的饭菜。
孩子处在被植入“奴性”的环境中。首先,他们需要父母的养育。没有父母的关爱他们就活不下去,所以他们不得不听父母的话。如果不听话,就要被打上“小混混”“坏孩子”“不惹人爱”等烙印,内心备受煎熬。若不是内心特别坚强的孩子,绝不可能坦然接受那些指责。孩子注定无法逃离父母,所以父母只要有意,就能以这个事实为筹码对孩子为所欲为。
4卧床不起的母亲用二尺长的尺子责罚我
母亲罹患了脊柱骨疽,其后卧床六年,直到卡那霉素这种药问世。这种病是因为结核病菌侵入骨骼,导致骨头溶解化脓,引发身体障碍,治疗时医生需要用注射器吸出脓水。吸脓时身上会有个大洞,溶解的碎骨渣哗啦啦地往外流淌。可以说,母亲一直处在垂死的状态。
母亲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为了让我能够独立,她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我能有一技之长。她自己在疏散到乡间居住时也曾尝试学习裁缝手艺,可是按她的说法,不能留我一个人在敌阵之中,所以最终半途而废,无法自立谋生,并因此悔恨不已。她一心认定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无须忍受那样的屈辱,所以母亲的愿望就是让我好好学习,成为一个能够自立的人。
母亲当时已经卧床不起。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但是母亲什么都做不了,无法尽到为人母和为人妻的职责。不仅如此,她还面对着随时可能死去的威胁。她必须在那种情况下使我能够自立,想必内心是很焦急的。
她卧床时需要用石膏架固定身体,因此无法动弹。于是她在身旁放了一把二尺长的直尺,用它来责罚我。我必须待在那把直尺能够触及的范围之内,母亲打我时绝不能躲开。要是我躲开了,母亲就会大发雷霆、发起高烧,导致病情加重,所以我绝不能躲开。
有一次母亲气急了,甚至把我的教科书撕成两半扔出窗外。当时,教科书在我眼中就像基督徒的《圣经》那样神圣,因此这件事令我万分痛苦。也许我的心也随着教科书被撕成了两半。
后来母亲的病稍有好转,一家人偶尔会出门旅行。每次回家后,她都会总结我那一天的行动。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姿势走路了,用什么语气说话了,用什么动作吃饭了,在什么地方大声吵闹了……我的一举一动都成了母亲的批判对象。如此反复下来,我变得特别在意自己的行动,最终什么都不敢做了。因为一做点什么事,我就特别害怕母亲的批判。母亲总是说:“我是因为爱你,希望你将来成才,才这样训斥你。”但是她的话语对我而言,就像折断树枝一样一根一根折断了我的手脚。
我渐渐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心情,只能把种种思绪拼命压抑在心中。我压抑了愤怒,压抑了悲伤(因为流泪会挨骂),也压抑了寂寞。即使放学了我也不想回家,经常独自呆立在操场中央。有时我也会去教学楼天台。我害怕回家,但又不知道能去哪里。这就是我每天的心情。
5压抑的轮回,造就了家庭版“霸凌结构”
我弟弟长得像母亲,是个双眼亮晶晶的可爱的男孩子。母亲很喜欢可爱的弟弟,常给他试穿我的红色和服,还总说如果弟弟能跟我换一换就好了。我虽然遗传了父母不好看的地方,但是看我两三岁时的照片,也是个挺可爱的女孩子。然而上小学后,我渐渐变得乖戾,神情也越来越阴暗,母亲就说:“咱们家没有你这样的,我没生过你这么丑的孩子。”长得丑就算了,还是个傻大个,整天不听话,太讨人厌了,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我一直沐浴在这些话语中,承受着三重、四重的苦楚,渐渐磨灭了自信。
所以我觉得,母亲对我的爱其实与“霸凌”只有一纸之隔—隐藏在管教之下的霸凌。当时的我没有能力以第三方的视角审视这一切,更没意识到那竟是霸凌。我只想得到母亲的爱,认为母亲的责罚都是因为我不够好。但是现在看来,我十分清楚母亲为何要霸凌我。
母亲对孩子以管教为名、以教育为名、以爱为名的霸凌,其实与母亲自己的人生问题有很大的关系。母亲的生活方式会折射到孩子身上。只能为孩子而活的人,其人生是极度压抑的。被压抑的人一不小心就会把情绪发泄在比自己更弱小的人身上。
母亲处在无尽的压抑之中,找不到任何出口,肯定满怀无处发泄的怒气与怨气。她必须倾倒这些情绪,她想看到别人因此而痛苦。只有这样,她才能感到心情畅快。当然,这些心理活动都发生在潜意识之中。因为一旦变成表意识,那个人应该会主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一旦用霸凌的结构去分析它,就会发现家庭中也出现了跟学校一样的现象—被压抑的人、被霸凌的人转而去霸凌比自己更弱小的人。父亲在公司受了委屈,回到家中抱怨,或是殴打母亲,或是施以冷暴力。他还会对家中的开销和卫生情况挑三拣四。母亲遭到丈夫的霸凌,就会转头责骂孩子:“你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还不快去学习!”接着,孩子就会去踹狗。如果家里没有狗,孩子就在学校挑个看起来不会反抗的同学欺负。这就是霸凌的结构。
小时候,我最害怕的就是母亲。如果不听母亲的话就要挨打。那么挨打后我会欺负谁呢?答案是弟弟。
我经常被母亲要求带弟弟。我背着弟弟出去玩,大家看到他穿着红色和服,都会交口称赞“好可爱”,于是我就把弟弟放下来。趁着大家跟弟弟玩,我偷偷躲起来。弟弟发现我不在了,就哭着喊“阳子”。我躲在暗处看弟弟哭,自己也会哭起来。我一走出去,弟弟就高兴地跑过来,然后我就会特别高兴。
被我欺负之后,弟弟半夜会做噩梦哭闹。这时父母就会叫醒我,斥责我“又欺负弟弟”,然后将我赶出家门。有时在下雨天,我看到外面有人路过,总会冲动地想跟上去。在某个时期,我每天都过着这样的日子。父亲白天不在家,不知道母亲跟我之间发生了什么,所以会帮着母亲训斥我。
其实弟弟也不好过。他上了初中后,就经常被母亲拿来跟我比较。弟弟不太爱学习,母亲就每天骂他:“你怎么不学学阳子姐姐呢,一个男子汉不好好学习怎么行!”
所以我从小就见惯了霸凌的结构,深深知晓弱小的人跟被压抑的人待在一起会遭遇什么样的对待。
6讨人喜欢的人,都为了迎合而扼杀“自我”
我认为,母亲培养我独立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是她的管教方式对我而言就是纯粹的压迫。那时战争刚结束,根本买不到好吃的点心,所以不存在用点心“哄骗”的招数,我所接受的是这样的管教方式—“妈妈这么生气都是因为疼爱你”。很难说这究竟算不算“哄骗”,我可丝毫没有感到自己得到了疼爱。唯独“爱你所以打你”的矛盾组合,一直盘踞在我心中难以化解。
当然,年幼的我并不知道“压迫”这个词。我只是会经常做噩梦,每次梦到的内容都是地球重重地压在我的胸口。
那个时期,我还常常因为“生闷气”而遭到责骂。其实越是被压抑的人就越容易闹别扭、生闷气。当亲密关系中发生矛盾,一般都是立场更强的人主张自我,立场较弱的人哑口无言。立场弱的人即便有怨言也不敢说出口,这种时候就会生闷气、闹别扭,然后,还会哭泣。
我就是这样变得越来越乖戾了。因为在强大的母亲面前,我总是“祸从口出”,动辄得到一记光,或者被二尺长的尺子痛打一顿。一旦闹别扭,我的神情就特别阴暗。傻大个,长得丑,再总是闹别扭,那就真的无可救药了。这种时候母亲就会说:“你学习好有什么用,如果不当个讨人喜欢的可爱女生,今后就嫁不出去了。”
就跟上文提到的艾灸一样,艾灸是为了让我变成乖孩子,可是我乖乖忍受责罚又会遭到批判。我无法抵抗过剩的责罚,只能闹别扭以示抗议,一闹别扭面容就会扭曲变丑,这时母亲就说“不会笑的人不讨人喜欢,以后嫁不出去”。那我到底要怎么做?借用女性学研究者、生活艺术家驹尺喜美的话语,这种情况就像前方同时亮起了绿灯和红灯。
对年幼的我来说,讨人喜欢就是不想笑也得咧着嘴笑,心里说“不”,脸上也得说“是”,要不断看别人的脸色,做可爱的行动,绝不能表露真实的自我,要极力讨好别人。
所以,他人的爱让我感到极度压抑,不得不把自己压缩得很小很小。换一种说法,就是唯有把自己缩进极小的牢笼里,才能得到那种爱。只要“爱”保持在被动状态,我就不得不压抑自己去讨好别人。真实的自我没有任何价值。可是这样一来,真实的自我就会被全盘否定,使我再也搞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
我再也无法用心灵去感知事物,再也无法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
7无法逃离霸凌者的心理
我很想逃离母亲,所以考上大学,离开父母住进宿舍时,我觉得自己总算自由了。在此之前,我每日听到的话语都是“不准去那里,不准见那个人,做完家务去学习,学习再好有什么用,又不会帮店里做事,又不会做家务,长得不好看,不讨人喜欢的人就是不行”。因此,我特别想要属于自己的时间。我特别想尽快离开那个家,想一个人生活。
考上大学时我真的很高兴。可是母亲一打电话来,我就会哭出满满一桶眼泪。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哭成那样,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人一边想逃离霸凌自己的人,一边又想对那个人传达自己的心情。你为何不温柔地疼爱我?为何不理解我?为何在责骂之前不听我解释?我有那么多想说的话,父母却充不闻。“都是你的错”“是你不够好”“你太笨了”,每次都在重复同样的谩骂。希望父母理解我—这个渴望也会转变为某种形式的爱。当自己从霸凌式的关心中解放出来,我除了有自由的感觉,还会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这太令人费解了。即使面对自己最想逃离的人,在承受了将近二十年的霸凌后,我还是忍不住怀念她的支配。
对孩子来说,母亲是最重要的人。面对这个最重要的人,孩子渴望她的理解,因此拼尽了全力,但是孩子绝对得不到理解。母亲对孩子而言,就是上帝。
我十几岁时对基督教产生兴趣,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时还考虑过要不要成为基督教徒。当时我有一个观念,就是上帝绝不会回应我。因此,人们要研读《圣经》,努力领悟如何得到上帝的宠爱。遵守教义,努力改变自己,重新塑造自己,让自己成为不倒翁;不断地讨好上帝,疯狂地崇拜上帝,疯狂地渴望得到理解。然而,上帝始终沉默。于是,人们只能自发地去理解上帝。基督教上帝与信徒之间的关系,不知为何竟有点像母亲与我的关系。母亲与我之间,似乎是那种关系的缩影。对我而言,母亲是绝对的存在。母亲的训斥、管教与霸凌都有着爱的名义,但是她绝对不会理解我的心情。一旦我试图解释,她就会骂:“不准顶嘴!”如果我不说话,她也要骂:“你有什么资格生闷气?”然而,人还是会认为斥责自己、殴打自己的人深爱着自己,并紧紧跟随,逃不掉、切不断这份依赖。孩子无法选择父母,只能紧紧跟随。
经常能看见有些母亲在路边声色俱厉地训斥年幼的孩子。孩子连哭泣都忘了,小脸没有一丝血色,拼命抓着母亲的裙摆。那种光景背后总是隐藏着什么。孩子害怕被抛弃,不惜扼杀自己,也要努力听父母的话。
8一边洗碗,一边因身为女性而流泪的母亲
离开了家,与母亲拉开距离后,我终于能够深入思考自己与母亲的关系。然后我发现,那个借管教之名霸凌我的母亲,其实也承受着跟我一样的痛苦。
母亲也对她的母亲(我的姥姥)心怀憎恨。她更喜欢自己的父亲(我的姥爷)。问其理由,她说因为姥姥对她太严厉了。姥爷反倒很温柔,很疼爱她。
可是,母亲并没有把“我讨厌母亲是因为她太严厉”关联到她自己对孩子的严厉态度上。就算真的关联了,她可能也无法抑制内心涌出的那股巨大的力量。因为母亲自己身为女性,只能顺应并选择社会普遍认可的女性的生活方式,她为此悔恨不已。
战后,母亲因病长期卧床,为了挖苦父亲,经常炫耀自己在新潟县的娘家。她说娘家住的是当地、最气派的房子,别人都穿棉布衣服,自己却能穿真丝的铭仙和服。每次炫耀完娘家,她都要哀叹自己的不幸:“为什么我偏偏要过这样的日子?”她还很疑惑,娘家明明这么好,“为什么不让我接受教育”,并因此对她的父母怀恨在心。
我的父母是左邻右舍公认的好夫妻。母亲年轻时,家里给她谈了亲事,都已经走到收聘礼的阶段了,她却坚持不愿意嫁给农民,推掉了那桩亲事。她逃出来去了伪满洲国,并在那里结识了父亲,与他结为夫妻。战后,父亲一边经营酒馆,一边照顾发病的母亲,还要空出手来养育我和弟弟。
母亲虽然卧病在床,但也像个女王一样作威作福。她一边念叨“明天就要死了”,一边盛气凌人。她在年幼的我眼中就是这种感觉。父亲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似乎觉得那样的母亲很有魅力。因为她真的很厉害,明明随时都有可能死掉,一天到晚都要依赖别人照顾,但绝不会委屈自己。我猜,母亲其实已经因为疾病耗尽了精力。她沉浸在延绵不断的痛苦和绝望中,也许对人生充满了狂热的愤怒。刚活到三十岁就要死了,她应该特别不甘心。
偶尔身体状态还算好的时候,母亲就会自己起床化妆,然后进厨房做事。我到现在都忘不了,母亲曾经流着眼泪洗碗。她边哭边说:“为什么只有当妈的要从早到晚给碗擦屁股?”
看见母亲哭泣,对孩子来说可谓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个总是严格管教我的母亲竟然哭了。同时我也想,她好不容易精神一点了,洗碗不就是妈妈的工作吗?因为她病了,本来不用洗碗的爸爸每天都要洗碗呀,可是母亲却说:“为什么只有当妈的要这样?”
9女人只有枷锁之下的自由
只要身体稍微有所好转,母亲就闲不住想做事。她想盖一座更大的房子,想买下那块便宜的地皮做点生意。然而,就算母亲说了想做这个想做那个,父亲不同意就什么都做不了。父亲要照顾得了大病的母亲,很担心母亲哪天身体再垮掉还得花钱,所以一直都不答应。
从母亲的角度看,她虽然得到了精心的照顾,但是自己想要做点什么,需要用到家里的印戳时,得不到父亲的首肯就无法实现,这恐怕让她很不甘心。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三四十年前,办正事用的印戳是只属于父亲这个一家之主的。这就叫作父权制。
母亲得到了丈夫的精心照顾,但也只是比那些任劳任怨的妻子自由一些,项上枷锁松了一些。她肯定还是有着真切的感受,知道自己依旧是被豢养的人。母亲甚至说过:“只要盖个印就能弄死我。”这么说也许很夸张,可是拥有印戳的人确实能够左右女人的一生,能够彰显主人的身份。母亲亲身体会到了一个男人只要为人丈夫,就能靠一个印戳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
尽管如此,在父亲死后,母亲还是一直对他感恩戴德。父亲去世的头三年,她每天都清洗他的衬衫挂出去晾晒,每天都为他准备阴膳1合掌悼念。然而,我有一次开玩笑地问她:“你下辈子还跟爸爸结婚吗?”母亲却明确回答了“不”。父亲去世后,她的态度就变成了“男人?结婚?NO!”。看来她已经有了深入骨髓的感触:尽管丈夫如此珍爱她,她最终还是被一手掌控的存在。母亲是个非常自我、性子暴烈的人,肯定早就看出了这里面的问题。她只不过是幸运地遇到了不会殴打她,反而会疼爱她的丈夫。
小时候听到的“为什么只有当妈的要从早到晚给碗擦屁股”“只要盖个印就能弄死我”这些话深深刺痛了我的心。随着我慢慢长大,我终于接触到了这些话所揭示的世界,也体会到了母亲的那份痛苦。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母亲的那些话语。母亲与我虽是霸凌与被霸凌的关系,但是从女性的立场出发,那些话会让我牢牢记住,我与母亲都站在同样的基准之上。当我对自己身为女性主义者感到迷茫、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会默默咀嚼着那些话语,给自己鼓劲。
我在疏散地的“吃鱼事件”中体会到的屈辱,还有母亲说的那些话,都可以总结为迫不得已寄人篱下之人感觉到的屈辱。因为被豢养,所以不得不给碗擦屁股。女人只有枷锁之下的自由。女人只能通过婚姻存活下去。女人都是被豢养的,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她们没有选择权,没有自主决定权。母亲的话语在各种意义上成为我的人生警钟,还向我提供了研究的方向。
我是母亲在痛苦的生活中用作发泄的出口。我花了漫长的时间疗愈自己被伤害的心灵,同时一直在思考自己为何被当作发泄的出口。也许可以说,这本书是对我思考过程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