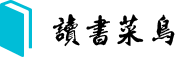《漫长的调查: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萧易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
内容简介:
1939年8月—1940年2月间,梁思成领导的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西康走访了35个县市,拍下3100多张照片,这就是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也是营造学社历时最久的一次调查,共173天,却一直鲜为人知。
本书沿着当年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路线,重走考察之路,将营造学社的调查对象一一考证,重现当年梁思成与他的同伴们的考察经历,结合营造学社拍下的调查照片与今天的现场照片,让读者再次看到川康古建筑的过去与现状。全书约15万字,图约260张,以营造学社当年的考察路线为顺序,兼及地域特色划分章节。
作者简介:
萧易,作家,曾出版《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影子之城》《空山——寂静中的巴蜀佛窟》《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古蜀国旁白》《纵目神时代》《金沙》《石上众生——巴蜀石窟古代供养人》等专著,即将在本社出版《中国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图录》等。
目录:
成渝之间
陪都前后的山城重庆
从明蜀王府到陈举人府
安澜索桥
中国第一竹索桥的前世今生
西康纪行
“汉阙翘首”高颐阙
芦山访古
太守、将军与县令
沿江南下
破镜重圆的夹江千佛岩
白崖崖墓
祠堂中的汉代春秋
与营造学社失之交臂的宋元建筑
彭山崖墓
石头上的建筑史
寻找明代平盖观
北上蜀道
新都古寺三绝
唐塔、梁碑与明构
拼接西山观
中国最大的道教石窟群
重返金牛古道重镇梓潼
广元
武后皇泽千佛重影
东行嘉渠
阆中
穿行在唐代梵音中
南部禹迹山大佛
蓬溪县
鹫峰寺 定香寺 宝梵寺
穿行在汉阙之乡
石窟之乡
潼南石窟
大中八年四娘遇贼记
“得而复失”的大足石刻
濮岩寺
石窟里的合州刺史们
内迁李庄
板栗坳
史语所李庄往事
戎州故城旧州塔
拼接观音寺
一座明代寺院的营造与重现
广汉照片中的古城标本
编辑推荐:
★尘封数十年,营造学社不为人知的旧照重见天日 中国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鲜为人知,其调查时拍摄的大批照片更是到21世纪才被人们重新发现,我社由此策划出版《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图录》(共6卷),为首次公开出版这一批珍贵的照片。本书选取这套图录的精华内容,着力展现营造学社用脚步丈量的古代中国。
★海量旧照与今昔对比,凝结数十年来的历史变迁 当年,梁思成与他的同伴们克服各种艰险,用173天穿梭在巴蜀大地上,用3100张照片留下了中国古建筑瑰宝的身影。八十多年后,本书引导读者找寻到这段历史,以两辈人的视野,注视那些崖墓、汉阙、建筑、城市——它们,有的还在地上,有的,已在纸上。
★知名文物古迹探访者对先行者足迹的追寻 作者萧易十几年如一日积极参与对文物古迹的走访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创作了许多作品,这份经历在本书中有深刻的印记。书中展现了他对古建筑及其相关文化历史的深入了解,而作为同样“行万里路”的调查者,他对这段八十年前的旅程如同跨时空对话般的感想亦相当值得关注。
前言:
序
中国营造学社八十多年前在四川调查的3000多张照片,今年 整理汇成《中国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图录》(六册)出版。萧易还根据重走当年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路线的见闻,写下了这本《漫长的调查》。
1939年秋季至1940年2月,父亲梁思成和刘伯伯刘敦桢率队,带领莫宗江和陈明达二位先生到四川省和西康省进行了一次范围广泛的古建筑野外调查。半年中他们走过35个县,调查了730余处汉阙、崖墓、摩崖、古建等。与此同时,母亲林徽因和刘致平先生留守在昆明乡下的麦地村,在一座叫“兴国庵”的小庙里开展学社日常工作,兴国庵大殿成为临时的古建研究工作室,木架支撑起一块木板成为绘图台,上方立着几尊菩萨,工作台与菩萨们共处一殿。
他们首先考察了重庆、成都及周边的古建筑,当时日本敌机在四川狂轰滥炸,考察工作只能在警报间隙中展开,趁着警报稀疏时扛着仪器出城或返回。行走在兵荒马乱之中,他们随身都携带着由重庆市政府颁发的护照,以备军警时时盘查。父亲的护照上写着:“为发给护照事,兹有中国营造学社社员梁思成,现年三十九岁,广东新会县人,由重庆到 调查古建筑遗迹,特发给护照,希沿途军警查验放行勿阻,该持照亦不得携带违禁物品,致干查究。”这一路,他们往返于岷江沿岸、川陕公路沿线、嘉陵江沿岸,跑了大半个四川。
四川省的木构建筑大多毁于“张献忠之乱”,但境内保存了大量的汉阙,其总数约占全国汉阙的半数以上。崖墓数量也很可观,在岷江、嘉陵江两岸,崖墓时而散布,时而集中,随处可见。最多的要数摩崖石刻,那里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摩崖石刻的县城。虽然学社没有找寻到明清以前的木构建筑,但大量的石阙、崖墓均反映出汉代建筑的营造法式,这是华北地区所难见到的。
摩崖石刻中往往刻画出人们想象中的西方极乐世界,以及其中各种类型的亭台楼阁,建筑各细部处理准确、比例逼真,它们是研究唐代木构建筑的宝贵资料。总的来说,川康考察虽然在木构建筑方面收获不大,但发现的汉阙、崖墓、石刻大大填补了建筑史中汉唐阶段的空白。
学社团队到川康两省展开野外考察期间,我们曾收到过父亲的来信,厚厚的一沓。那是十多张“考察连环画”,画面上他们走在郁郁葱葱的山林之间,脚夫们手上抬着滑竿,嘴里喊着号子。脚夫通常两个人抬滑竿,一前一后,后面的人看不见前路,全靠与走在前面的脚夫对话来实现默契配合。父亲的连环画记录的便是这样的场景。他的画将这些景象描绘得惟妙惟肖,读之如临其境:
前面脚夫喊:左边一个缺!(告知有个坑)
后面脚夫和:来官把印接!(官场术语,回答知道有坑)画上,正画着路前方有个不大不小的坑。他还把自己和刘伯伯都画了进去:脚夫们挑着滑竿前行,父亲在后面的滑竿上坐着,前面则是刘伯伯,他们听到脚夫文绉绉的号子,一时乐得前仰后合。读信的母亲、我和弟弟也笑得前仰后合。又见另一张画上写着:
前面脚夫喊:天上鹞子飞!(告知不要只看天,注意脚下)后面脚夫和:地下牛屎堆!(回答知道有牛屎)父亲的画上画的就是他和刘伯伯两个人被滑竿抬着,向远处眺望的景象。天空中还有鸟儿盘旋,前路上依稀可见一坨牛屎,正是脚夫们号子里喊的意思。
还有一张上画着:
前面脚夫喊:左边一大排!(相遇很多人)
后面脚夫和:一个一个数起来!(注意到来人了)这就是到了人多的地方了。我还记得父亲在画面的左侧画了一大排当地模样的各色人等,他们有的扛着菜,有的拎着筐,表情丰富各异,穿着也各不相同。
更有意思的是:
前面脚夫喊:左手一枝花!(前面碰到一位女士)后面脚夫和:没钱莫想她!
看父亲的画上,一位貌美如花的女士正从脚夫们身旁经过呢!
脚夫们一前一后喊着滑稽的号子,路上接连不断地发生着一系列故事,那画面真是被父亲描绘得妙趣横生。母亲看了开怀大笑,我和弟弟看得不眨眼睛。
这一叠西南考察时期留下来的连环画,画面生动,让人身临其境,如同亲耳聆听到脚夫的号子一般,一张张图画让全家人看得乐不可支,给我们当时凄苦寂寞的生活带了许多欢声笑语。几十年过去了,父亲画中那每一笔都令我记忆犹新。
1940年11月下旬,中国营造学社决定随同工作关系密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文简称“史语所”)迁往四川南部的李庄。由母亲带领全家(外婆、我和弟弟)与刘敦桢伯伯一家同行。父亲留下治病,治愈后再到四川来。
12月13日上午,我们从宜宾坐小木船(下水船)前往李庄,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离宜宾约60里的李庄。我们一家后来在李庄住了五年半,直到1946年夏天才离开。
李庄镇在长江南岸,是一个青山绿水、树木繁茂的地方。镇南有与长江平行的起伏山脉,不太高的小山上是成片的橘林和茂密的竹林,江边有多人才能合抱的大榕树和宽阔的草场,沙土地上生长着颇有名气的李庄花生。在物资匮乏的抗战时期,这里是一个得天时地利的好地方。因此,不仅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社会所、中央博物院以及营造学社等学术单位迁来了,同济大学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从云南迁来。一时间,这个小镇成了抗战时期后方人才荟萃的文化中心。
但是,李庄也是一个气候比较阴冷潮湿的地方。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其凶猛,连续几周高烧四十度不退,从此失去了健康。尽管她稍好时还奋力维持家务,继续协助父亲做研究工作,但她身体日益衰退,成为常年卧床不起的病人。
我们到达李庄后,立即前往离李庄镇约两里路的上坝村月亮田,中国营造学社的“社址”就在这里,也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在到李庄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我们的房很大很好,院里有芭蕉,我很高兴。我们都坐在树下,把芭蕉叶撕成一条一条的,编成凉席。晚上大家合在一起吃面,很是热闹。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另外一个地方,叫作板栗坳,社会所在门官田,中央博物院位于李庄镇的张家祠。叔叔梁思永是史语所的研究员,记得母亲那个时候身体还很好,乘坐滑竿去板栗坳看望三叔,回来跟我讲:
板栗坳好极了,大块大块的石板,大棵大棵的梅花、茶花,上五百五十五层台阶才到上面。
这一句我写在日记里头,印象还很深。在母亲的记忆中,板栗坳不仅建筑物漂亮,环境也非常优美。
2018年,萧易根据父亲与刘致平先生应广汉邀请拍下的560张照片,写成了《影子之城》一书,将小城广汉作为中国城市布局的标本,讲述建筑与城市、建筑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拉开了川康古建筑再次研究、调查的序幕。这几年,他重走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讲述了父亲与刘敦桢伯伯等人抗战年间一段鲜为人知的调查,也勾勒出了一个八十多年前的四川。照片中的很多地方,崖墓汉阙,石刻建筑,他都一一走过。零散的照片经由他之手,变成了一座座立体的建筑;八十多年的变迁在他的笔下,读来是如此亲切,却又触目惊心。
今天,我将所记得的有关四川的往事讲出来,权以为序。
梁再冰 口述 于葵 执笔
2023年6月11日
在线试读:
逆时代的173天
姿态优美的西桥横跨两岸,桥上行人如织,冬日西河干涸,露出河底凌乱的条石,附近的百姓在一汪汪水塘中洗衣择菜,用四川话摆着龙门阵,儿童埋头在石块中搜索着漏网的铜钱。梁思成走到桥下,凝视着西桥净跨十一米的拱券,一袭黑大衣的陈明达、手拿测绘本的莫宗江也跟了过来,夕阳将他们的影子映在厚实的桥墩上。拍摄照片的是刘敦桢,时任中国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
这一天是1940年1月4日,南充县,照片中的西桥也称广恩桥,始建于宋代,清嘉庆年间重修。此时,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一行已走过重庆、成都、灌县、雅安、芦山、夹江、彭山、乐山、新都、广汉、绵阳、梓潼、剑阁、广元、苍溪、阆中、南部、渠县等地,川康古建筑调查到今天已经130天了。
看似恬淡的画面背后,是一寸寸山河沦陷。全面抗战已经进入到第四个年头,就在1月4日,日本人叫嚣“无论如何,今年要解决中国事变”。而在四川,交通不易,人心浮动,城市中的古建筑年岁已久,却因战争、贫穷无力维护,纷纷走向破败。梁思成曾经不无感慨:“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
对于这次调查,读者或许觉得陌生,我们耳熟能详的是营造学社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调查。1932年,初出茅庐的梁思成与助手邵力工前往河北省蓟县,在这个山麓小城中,发现了“充溢着唐风的梦幻般的观音阁”;1932年6月,梁思成前往调查河北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当时被骑兵团占据,佛、菩萨隐藏在堆积如山的稻草中,殿中没有天花板,梁思成一下子明白了宋代建筑学著作《营造法式》中的“彻上露明造”是怎么回事;1936年5月14日—6月29日,刘敦桢、陈明达赴河南进行古建筑调查,5月28日梁思成、林徽因抵达洛阳,一同考察了龙门石窟,刘敦桢记录建筑特征,林徽因记录佛像雕饰,梁思成和陈明达负责摄影;1937年5月19日—6月30日,刘敦桢又赴河南、陕西两省,几乎与此同时,梁思成、林徽因正跋涉在山西,7月5日,他们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佛光寺——原来中国还有唐代木建筑!
1937年7月5日同样也是营造学社的分水岭。七天后,沉浸在惊喜中的梁思成、林徽因才在代县得知“七七事变”的消息,这也是他们颠沛流离生涯的开始。梁思成一家离开北京,先到长沙,再到昆明。1938年初,刘敦桢从老家新宁抵达昆明,他们的助手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先后抵达。营造学社的招牌在昆明重新挂了起来,员工也只剩下了五人,还有位不拿薪水的林徽因。
刘敦桢之子,东南大学教授刘叙杰回忆,梁思成、刘敦桢曾对学社的方向有过一次交谈,分别在手心写了两个字,打开一看,写的都是“调查”。梁思成、刘敦桢深知,只有不断地调查,才能了解中国的古建筑家底,即便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他们仍然把田野调查作为学社的方向。
1938年11月24日,刘敦桢带着莫宗江、陈明达,在云南西北部考察了大理、剑川、丽江、鹤庆、镇南、楚雄等地的古建筑,第二年1月25日返回昆明。不久,梁思成、刘敦桢又将视野投向了四川,酝酿一次更为久远的调查,因调查区域涉及四川省与西康省(1939年成立,1955年撤销),史称“川康古建筑调查”。
梁思成、刘敦桢均未回忆过考察缘起。内迁昆明后,学社的考察重心已从华北转移到了西南,放眼望去,整个中国尚未受战火茶毒的土地已经很少,四川算是其中之一。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不止一次从法国人色伽兰、德国人柏石曼的照片中,得见四川古建筑、古遗址的吉光片羽,迫切想一探究竟。对于四川省而言,这不啻于第一次家底的大普查,此前除了偶尔有外国传教士、建筑学家进行猎奇式的调查,国人对四川知之甚少。
1939年的昆明依旧空袭频繁,营造学社搬到了昆明郊区麦地村一所叫“兴国庵”的小庙。8月26日,刘教桢从瓦窑村来到昆明,购置旅行用品。在当日日记中,他写道:“此次赴川,拟先至重庆、成都,然后往川北绵阳、剑阁等处考察,自剑阁再沿嘉陵江南下,经重庆、贵阳返滇。”
营造学社的初步计划,是以川北金牛道沿线、川东嘉陵江沿线的调查为主。到了四川以后,他们发现抗战时期交通不便,短时间不易再来,遂不止一次调整考察计划,先是添上川南十五县,再增加大足、合川两县,行程由此多了四分之一。这也说明一个问题,营造学社最初计划的是“四川古建筑调查”,因计划变动才改为“川康古建筑调查”。
来到四川后,学社诸人一度非常失望,明末清初张献忠屠蜀,四川古建筑大多毁于兵燹,明代建筑都很少见,更别说宋元了。但四川有着丰富的汉阙、崖墓、石窟资源,学社调整方向,将这三个方面作为考察的重点。在9月18日的日记中,刘敦桢写到:“川中古建筑,以汉墓阙为主要地位,盖数量为全国现存汉阙四分之三也。此外,汉崖墓遍布岷江及嘉陵江流域,其数难以算计。而隋、唐摩崖石刻亦复不少。故汉阙、崖墓、石刻三者,为此行之主要对象。”
正如他们预料的一样,四川各地崖墓密如蜂巢,如蜂房水涡,尤以乐山、彭山两地数目最巨,乐山白崖崖墓规模恢弘,前带祭堂,镌刻着古老的汉代建筑图;彭山县江口镇一带崖墓超过四千座,不少门相带有硕大的斗棋。“西风残照,汉家陵阔”,中国现存汉阙46座,其中大半在四川,学社考察了雅安高颐阙、夹江杨公阔、绵阳平阳府君阙、梓潼贾公阔等,而在渠县,他们在土溪场、崖峰场一带就遇见了六处七座汉阙。最新的统计资料表明,四川有石窟2134处,是中国石窟最集中的省份,营造学社考察了间中涧溪口、青崖山,乐山龙泓寺等,这些石窟如今已全然不见踪迹。
如果说在华北考察的唐、宋、元、明古建筑帮营造学社梳理了唐代之后的建筑脉络的话,那么唐之前的建筑史如何书写?这个问题曾经在荣绕梁思成脑海中。而伴随着川康古建筑调查的深入,问题迎刃而解。梁思成提出了“佐证法”,即从汉闼、崖墓、石窟中寻找答案。梁思成《中国建筑史》中汉代部分的素材便明显倚重于四川的考察,他的另一本《佛像的历史》也对四川石窟涉猎颇多。
梁思成沿途还多有留影,我们熟悉的梁思成往往意气风发,或者与林徽因如同神仙伴侣,但照片中的梁思成却如此陌生。他灰头土脸,一脸倦容,在漫长的旅途中忍受着灰尘、阴雨、臭虫,以及日寇的空袭。刘教桢则有记日记的习惯。带着一本《刘敦桢全集》在重走的路上,如同跟他一同远行,天气的冷暖,行路的忧乐,旅馆的简陋,县长的脸色,在他的日记中五味杂陈。学社的两个年轻人,莫宗江与陈明达,经历了华北与云南的调查,已经具备了相对完备的学术素养,在此次调查中找寻着自己的学术方向,陈明达《汉代的石阙》一文即基于此次调查完成。
1940年2月16日,结束了长达173天的调查,学社回到麦地村。梁思成、刘敦桢或许不会想到,就在当年,日军登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决定内迁四川,一向依赖史语所资料的营造学社也不得不随之迁徙,他们又一次来到四川,这次到了南溪县李庄——一个当时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来到李庄后,学社生活困顿,林徽因终日抱病在床,梁思成不得不为了些许经费奔波在重庆与李庄之间。通常认为,在李庄的营造学社已无力进行大规模调查,但照片透露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线索——此时的学社依旧利用一切条件调查古建筑:1941年春夏之交,梁思成、刘致平受广汉县邀请,参与了重修《广汉县志》的工作;同样在1941年,刘致平调查了新都寂光寺、新津观音寺等明代寺院;1941年,梁思成出任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专门委员,8月完成了重庆府文庙修葺计划;1942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营造学社联合成立“川康史迹调查团”,对彭山县江口崖墓进行发掘;1941年与1945年,刘致平两次到成都,调查了南府街周道台府、棉花街卓宰相府、文庙后街杨侯爷府等,开中国民居研究的先河……在李庄,梁思成开始撰写构思已久的《中国建筑史》,川康古建筑调查的雅安高颐阙、彭山崖墓、大足北山石刻、梓潼七曲山大庙、蓬溪鹫峰寺等皆收入其中。但遗憾的是,这批资料此后一直随学社辗转流离,被静静压在箱底,未能得到系统整理,也就很少有人知道这次漫长的调查。
时间来到2008年,央视编导胡劲草拍摄《梁思成 林徽因》纪录片,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档案馆发现一个蓝布包裹,里面有560张四川广汉的照片。根据这批照片,我撰写了《影子之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并与三星堆博物馆、成都博物馆举办了“影子之城”特展。
整理照片时,我发现梁思成先生遗孀林洙女士手中保存着一份完整的川康古建筑调查照片,数目超过3100张。经由林洙授权,在四川省文物局支持下,我与各地文物局、文管所一起,于2019年春天开始重新调查营造学社当年考察的古建、古迹,了解它们的状态。八十年弹指一挥间,很难想象它们经历了怎样的命运。
西山观在绵阳城外凤凰山上,当年,瘦弱的道士领着他们,探访后山石窟,茂密的藤蔓遮住元始天尊俊逸的脸庞,真人的身躯掩埋在泥土中,破旧的香炉已很久没飘过香火了。如今的西山观成了西山公园,两个石包上残存31龛隋唐道教石窟,可惜的是,超过50个隋唐道教龛窟已不翼而飞,其中就有珍贵的大业六年龛。
1940年1月,梁思成一行来到蓬溪县鹫峰寺,这座寺院天王殿、大雄股、毗卢殿均建于明代,寺院左侧,一座挺拔的宋塔拔地而起。20世纪80年代,鹫峰寺几经波折,天王殿搬迁到了赤城湖清幽岛,大雄殿先是搬到钟山,又因开发房产被拆掉,在库房中存放了几年,直到几年前才再次组装复原。
文庙、武庙、广东会馆、陕西会馆、湖广会馆、城隍庙、娘娘庙、土地庙、开元寺,壮观肃穆的牌坊,样式精巧的桥梁,不同姓氏的宗祠……两临广汉,营造学社几乎拍下了这座小城内外的所有古建筑。如今存世的却不足十处。
拿到照片时,它们仅有简单编号,比如新津观音寺,编号从1—177号,但某张是属于哪个殿堂,抑或是殿堂的哪个部分,却无从得知。更糟糕的是,许多殿堂已经从观音寺中消失,无从依据,我们只有从前人调查、村民的回忆中找寻蛛丝马迹,或者是从照片的细节中寻找关联,将不同的照片拼接成殿堂,再将殿堂组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观音寺。3100多张照片,如同一幅巨大的拼图,让我们得以用一处处石窟、一座座建筑、一处处遗迹拼接出一个八十多年前的四川。
绵阳西山观消失的50多龛造像是什么?营造学社为何每每与宋元建筑擦肩而过?大足石刻为何得而复失?新津观音寺为何从十二重变成了如今的五重?中国抗战年间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在哪里?
川康古建筑调查的730多处古建筑、古遗址,或毁于兵赞,或没于土改,或亡于“文革”,或逝于城建,如今留存下来的已不足一半。重走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既是对它们命运的梳理与交代,也是对营造学社这次漫长调查的回顾——当年,他们逆时代的洪流,用了173天穿梭在巴蜀大地上,留下时代的背影。我们也在漫长的八十多年后才找寻到这段历史,经过五年的调查,我基本弄清楚了照片中古建筑、古遗址的状况,主编了《中国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图录》(六册),并把这几年重走的经历,写成了这本《漫长的调查》。那些崖墓、汉阙、建筑、城市,它们,有的还在地上。有的,已只在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