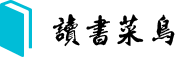《日暮时分》,[韩]黄晳暎著,徐丽红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4年9月出版。
内容简介:
“我们以前住过的地方,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成为记忆中的标本。过去的永远不会再回来,留下的是什么?”
当记忆不由自主地袭来,朴敏宇回想起那个他以为已经被抛在脑后的世界——覆盖整座山的低矮的石板屋顶,错综复杂的狭窄胡同和聚集在小店门前的孩子们的笑脸。
驱赶,拆除,重组,霓虹掩住星光,水泥代替土地。他不停地追逐向阳地,庆幸自己逃离了简陋龌龊的贫民区,从不好奇那些被从家园赶出来的故人,去了哪里,又以什么为生。当停下脚步,猛然回头,身边空无一人,记忆里的故乡无迹可循。
一往无前是开拓者的姿态,不将背影留给他人,被抛下的就是自己;不毁灭旧的世界,就无法到达新的乌托邦。羁绊越来越少,目光越来越冷,最终只剩回忆,陪伴生命迫近傍晚的自己。
作者简介:
[韩]黄晳暎
1943年出生于中国长春,童年经历战争,颠沛流离,有过流浪、打工、出家、当兵、流亡的经历。他的一生可以说是韩国近代历史的缩影。苦难的经历和曲折的命运让黄晳暎和国家、民族保持历史的同步,并以磅礴的文学世界贯穿了韩民族乃至朝鲜半岛的命运,他也由此被认为是韩国文学巨匠和最有可能代表韩国文学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作家。
年过八旬的黄晳暎仍在孜孜不倦地创作,他的主要作品有《客地》《去森浦的路》《韩氏年代记》《日暮时分》《熟悉的世界》《铁道员三代》等。曾获万海文学奖、大山文学奖等多项韩国权威文学奖项,其中《日暮时分》获2018爱弥尔·吉美亚洲文学奖,入围2019年国际布克奖,《铁道员三代》入围2024年国际布克奖。其作品被广泛译介到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享有盛誉。
目录:
导读:韩国文坛有位“太史公”
日暮时分
作家的话
名人/媒体评论:
黄晳暎是当今亚洲小说zui有力的代言人。如果让我说谁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我想说的是土耳其帕慕克、法国克莱齐奥、中国莫言和韩国黄晳暎。——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日]大江健三郎
韩国文学非常值得一座诺贝尔文学奖,就我个人而言,黄晳暎是很有力的诺奖候选人。——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法]勒克莱齐奥
“如果说韩国作家里面有什么传统,我觉得就是黄皙映作家说的 ‘我站在去世者的这一边’。我们想要善待去世的人,其实等同于我们珍惜人生,我们珍惜生命。”——韩国著名作家 金爱烂
李沧东一开始就把如何摆脱黄皙暎小说的影响当作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并做出了努力。——韩国评论家 秦炯俊
黄皙暎是韩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社会边缘人士的有力代言人。——《素食者》英文版译者 德博拉·史密斯
这部小说所蕴含的生命深度是无法估量的。——韩国文学村出版社
黄皙暎的《日暮时分》是韩国社会的一个完美切片。——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编辑推荐:
这个世界还年轻,我的故乡却老了。房子、砖墙、羊肠小道都不见了,我出生的地方只剩下了树桩,全世界的故乡都消失了。
每个韩国人都知道的韩国国宝级作家,两次入围国际布克奖,韩国民众呼声最高的“诺奖”候选人黄皙暎代表作品首度引进!
韩国自己的“余华”,金爱烂、李沧东的文学引路人,穿越苦难而来的现实主义风格,克制冷静、凌厉深刻,能够改变你对韩国文学乃至东亚文学认知的重量级作家!
既是写韩国往事,也是写东亚百姓的共同记忆——他们被现代化的大潮淹没,被甩在身后,陷入冷漠而且孤独的困境,独自舔舐着被时代车轮碾压后的伤口。
如同在看贾樟柯的《山河故人》《三峡好人》,从拆毁故乡的“侩子手”和漂泊无根的“城市游民”双视角,揭露急速现代化进程中的拆迁和重建问题,剖析普通人的挣扎与异化。
2023年豆瓣年度译者、2023年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译者翻译家徐丽红担纲翻译;翻译家薛舟撰写独家长篇导读,深度解析黄晳暎的世界。
上一代的过去变成业报,构成了年青一代的现在。艰难的时代正在到来,我们应该及时地回顾过往。——黄晳暎
在线试读:
演讲结束了。
投影仪关掉,屏幕上的影像也消失了。
放在演讲台上的水,我喝了一半左右,然后朝着闹哄哄起身的听众走去。主题是“旧城区开发和城市设计”,来了很多人,大概是因为存在着利害关系。负责视听民间企划的科长带着我,我跟在他后面来到礼堂外的大厅。所有人都背对着我这边,走向门口。有位年轻女性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我面前。
老师,请稍等。
她穿着牛仔裤和T恤,很普通的打扮,没有化妆,一头短发。我停下脚步,看了看她。
我有东西要转交给您。
我一头雾水,看看她,又看了看递到我面前的纸条。上面写着小小的数字,像电话号码。
这是什么?
我接过纸条问道。她犹犹豫豫,一边后退着远离我,一边说道:
您很早以前就认识的人……让您一定要给他打电话。
没等我继续追问,那名年轻女性就已经消失在人群中了。
我去灵山邑是因为尹炳九妻子发来的短信。他是我的竹马故友。我在故乡灵山读完小学,尹是住在我们家后面的同级生。住在镇上的人们大都在中央大马路拥有自己的临街店铺,或者是在郡政府、学校、邑事务所等地工作的人们。住在院落宽敞的方正韩屋里的人们是地主,到处都有自己的农田。父亲是邑事务所的秘书,拿着微薄的薪水,养活妻子儿女。
灵山位于洛东江桥头堡内侧,即使战争席卷而过,这里还是和从前没什么两样。父亲从战场归来,在邑事务所谋了个职位。听母亲是说,这都亏了父亲在某次高地战斗中立下战功,获得过勋章,还在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郡政府做过使役。在清一色务农的小镇年轻人中间,父亲读完小学,还学会了日语和汉字的读写。父亲的小炕桌上整齐地摆放着边角已经变色发黄的《六法全书》、《行政学》等旧书。后来离开农村去了城市,父亲在代书所做书记,也是这个缘故。虽然我们很贫困,不过每个月都有父亲的公务员工资,还有外婆家的小块农田,每年都能产粮食。那五亩水田是母亲出嫁时从外公那里分来的嫁妆。
我们住的房子位于小镇边缘山脚的坡顶。房子是一字型,三个房间,中间是厅堂。炳九家地势更高,跟我们家隔着一道砖墙。两间房子,再加上厨房,简直就是个窝棚,最初土墙草房,后来才更换了石板瓦。炳九是我儿时的好朋友,不过我并不了解他。小学毕业后,我们全家离开灵山,搬到了首尔。再次见到他已经是几十年之后,我们快四十岁了。那是在首尔市中心某酒店的咖啡厅里。
认出我是谁了吗?
他用庆尚道方言问我的时候,我想不起来他是谁。当时他穿着藏蓝色的西装,衬衫领子露在外面,很像官署里的高官。他刚说出尹炳九这个名字和灵山邑,那个早已忘却的外号就从我嘴里神奇地溜了出来,像中了魔法似的。
烤地瓜,你是烤地瓜吧?
即便是血肉之亲,时隔二十多年再见面,也会相对无言。大多只是问问家庭关系和现状,自然而然地喝着咖啡,交换名片或联系方式,有口无心地相约什么时候见面喝酒,然后分开。也许一辈子都不再见面,也可能通几次电话,哪怕以后再见面喝酒,也会觉得没意思,坚持不了太久。每个人都受困于各自的利害关系,如果这些关系没有交叉点,即使亲戚之间也只能在祭祖的日子见面。尹和我开始延续新的关系,是因为我在贤山建筑公司,而他刚刚接手了很有实力的建筑公司,岭南建设。看我还记得他的外号“烤地瓜”,尹炳九的眼角立刻泛起泪光,猛地抓住我的双手,结结巴巴地说,你还没忘啊。
我们家院子的左侧围墙边有棵合抱粗的榉树,他家就在这道围墙的后面。每天早晨他隔着围墙探过头来,喊我去上学。他家附近是村庄尽头的国有土地,也是小松林开始的斜坡。战争结束,附近佃户因为自己耕种的土地被收走而陆续聚集起来,凑合着用泥土和石头砌墙,搭建起了小窝棚,慢慢地就有了十几户人家。他们包揽了镇上的零活,做泥瓦匠、木工,帮着郡政府干杂事,每到秋收时节就去周围农村做帮工。我也出生在那些房子里,炳九搬到我们家后面应该是在小学三年级,不过我不是很确定。搬家那天,他主动跟我打招呼,我们在后山玩了一下午。炳九的妈妈为人很温和。我还记得她帮着农家挖地瓜,带回许多散落的地瓜,还送来一瓢让我们也尝尝。尹炳九经常带上两三个地瓜到学校当午饭。他的父亲不知道去了哪里,很长时间都见不到人影。每次回家都酩酊大醉,吵吵嚷嚷或者对妻子大打出手。听说他在附近城市的建筑工地当工头。
我之所以忘不了尹炳九,是因为我们曾在后山烧火烤地瓜,结果引发了山火。我们忙着给滚烫的地瓜剥皮,稍不留神,火花引燃了干草。我们手忙脚乱地追赶火苗,又是用脚踩,又是脱下上衣抽打,试图灭火,然而转瞬之间火势就蔓延到四周。我慌忙跑下去,大喊山上失火了。几十个大人从家里跑出来,涌到后山,乱糟糟地忙到天黑,总算扑灭了山火。
混乱之际,我和炳九藏到了郡政府前的公共礼堂。公共礼堂是日本侵略时期的神社所在地,后来用作礼堂或跆拳道场。我们在黑漆漆的公共礼堂里背靠背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