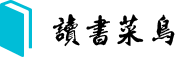到唐代时期,诗歌创作由魏晋南北朝注重对物象的刻画,发展为对意象和意境的表现,诗学理论也出现了对意境的探讨,如王昌龄的《诗格》、皎然的《诗式》等,其中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以下简称《诗品》)是研究意境不可忽视的诗学理论。《诗品》以诗论诗,用充满感性形象的语言对二十四种诗境风格的表现以及创作方式都进行了诗性的阐释,展现了主体心灵在文学创作中对宇宙之道的体悟与表达。《含蓄》是《诗品》中研究意境美的重要一品,它涉及意境建构的言语与意义、形象与内在、把握与表现等诸多问题,其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定义更是直接抓住了意境美的精髓。本文将通过对《诗品》中《含蓄》一品的释义,阐述“含蓄”的重要内涵,进而探究“含蓄”与意境美建构的关系,以便更深入地把握意境的美学特征。

一、对“含蓄”的释义
《诗品·含蓄》原文:“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
“含蓄”,与直白浅露相反,指内含深厚意蕴而不完全外露,言中有意而意不尽。杨廷芝在《二十四诗品浅解》中对其解释为:“含,衔也;蓄,积也。含虚而蓄实。”含蓄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以虚的形式表现实的内容。追求含蓄的诗歌表现最早可以在先秦的“温柔敦厚”诗教观窥见苗头,但这里的含蓄更多是出于维护礼制政治的需要,与《诗品》中所说的含蓄有很大差别。真正启发了含蓄审美思想的是佛道思想。两汉以后传入的佛教思想在南北朝时盛极一时,佛教的顿悟、心相、境界等超越性思想进入文论和诗歌创作。同时,道家思想在经历了魏晋玄谈之风后,将人们引向对形而上的宇宙自然的思考,当时盛行的玄言诗就体现了诗歌创作从外在现实脱离走向内在的抽象思辨。这些变化都促使文学创作和诗论发生转向,具体文字之外有着不确定性的含蓄之义进入诗人和文论家们的视野。例如,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隐秀》篇,就注重文字形象之外的旨意。到了唐代,佛禅思想更是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和诗论,如王维的山水诗、王昌龄的诗境说等。晚唐以后,昏暗的现实政治使得许多人隐逸山林,在佛道思想与隐逸的影响下,以司空图为代表的诗人个体情感更加向内收缩,重新回到老庄“言不尽意”的状态。因此,司空图所说的含蓄不是独创,而是对一以贯之的古典诗论的发挥。下面结合《诗品》具体诗句对《含蓄》一品进行阐释。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此句是对含蓄的核心定义。“风流”是能体现宇宙中万事万物生命性和精神性的本质所在,不用具体的文字形容,事物的风流韵味就能完全表现出来。诗是一种感性思维的创造,文字的能指与所指一一对应,在表达超出文字已有的所指意义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清人翁方纲的《神韵论》指出“不着一字,正是函盖万有”,需要在有限的文字中表达无限丰富的意义。首句表面上说的是语言和形象的关系,实际上是言、象、意三者的关系。真正含蓄的作品应该是能让读者忽视文字的存在,透过文字中生动鲜活的事物或情感形象的暗示来把握作者深藏的无限之意。
“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此句是对含蓄的艺术感染力的阐发。文本内容不涉及自身,但其中传达出来的忧愁悲苦已经让人觉得无法忍受了。上一句从宏观上宇宙之道的根本性方面理解含蓄,这一句就过渡到含蓄的效果在人的主体情感上的表现,人的心性情感是宇宙中灵气的凝结,从宇宙到人心体现了天人合一内在生态的互动交流。含蓄的作品不直接表露苦痛就能让读者感同身受,深刻体会文字之表以外的情感体验。含蓄的效果建立在人的同理心之上,它在个性的自我情感中触发共通性的东西,引起同一文化心理构造的共振,进而才能使人置身其境,这种共通性的东西就是“真宰”。
“是有真宰,与之沉浮”,此句紧承上句,解释了含蓄发挥作用的根本所在。在含蓄的作品中,外在文辞必须以内在充实的思想意蕴为主宰,使之自然而然表现于文辞中,随着文辞的变化而若隐若现。郭绍虞指出此句出自《庄子·齐物论》中的“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真宰”和道、自然联系在一起。因此,“真宰”不仅指作者思想情感的主体性,还指向宇宙自然的根本规律,即万事万物之所以这样或那样运动变化的道。当创作主体真正把握了道,在道的统领下形成自己主体性的思想,也就能领悟到创作对象自然造化的本真特点,并在有限的文辞中表现出来,而道是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它只能在文辞中若隐若现被感受到,而不能凭借理性得知全貌。
“如渌满酒,花时返秋”,此句是对含蓄的形象化表述。含蓄就像发酵的酒满了以后不断渗出的状态,也像花朵正当春暖之际忽遭寒风而将开未开的姿容。郭绍虞认为“如渌满酒”是渟蓄态,“花时返秋”是留住状,都准确地抓住了含蓄的特点。有渟蓄,有留住,说明含蓄之下有着丰富深厚的意义内容,流露出来的小部分吸引着读者去体味探求更深层的部分。含蓄的作品不需要将要表达的意思和盘托出,而是通过想象性的形象整体,就像句中的酒和花一样包蓄在内,自然会有风流溢出言表。因此,在遣词造句中有收有放、有行有止,使得意义更加蕴藉地表达,方能余韵悠长,耐人回味。
“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此句是对含蓄的进一步譬喻。含蓄包纳的内容广远无边又变化无穷,如空中的尘埃漂浮无定,海上的水泡变幻无穷。天地之间万物形形色色的样态并不能在文字中全部呈现,但借助含蓄的表达手法建立的意义空间就能赋予同一对象以不同的样态,让读者通过文字想象形象。这就要求创作者能从对生活的观察中体会到对自然万象进行统摄收纳的表达,既能化繁为一,透过纷繁杂多的万事万物把握本质性的造化,又能化一为繁,以含蓄的手法表达丰富的内容。
“浅深聚散,万取一收”,紧承上句,最后一句是对含蓄的创作方法的总结。这句涉及如何以有限的形象传达丰富的意义的问题,关键在于“万取一收”。乔力在《二十四诗品探微》中对“万取一收”有比较确切的解释:“因生活和艺术的积累既博且厚,大千世界纷繁总杂的事物无不可供我驱策选用,是谓‘万取;而经过精心剪裁熔铸,以凝练的手法和简洁的语言,勾画出优美生动的意境:形象鲜明,包蕴丰富,韵味无穷,是谓’一收。”创作者在面对广阔天地的素材时,需要根据自己思想情志的主宰对素材进行精炼提纯,选择最精华的形象来呈现丰富的内容。我们常说的意象就是诗中以一总万的形象,具有事物多样性形象的客观属性和创作者思想情志的主观属性,单一的形象不能称为意象,由多个意象共同构成的意境就是含蓄“一收”而形成的意义空间。
二、意境中的“含蓄”
随着佛教的“境”与老庄及玄学思想杂糅,意境说在唐代尤其是盛唐以后形成并发展兴盛,在晚唐司空图的《诗品》和其他诗歌理论思想中达到一个高峰。在《与李生论诗书》中,司空图论及了“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审美趣味,区分了诗歌文本的可尽之意与言表之外的不尽之意。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司空图提出“思与境偕”的创作论,“境”是融合了主体思想情感的审美时空,包含了众多物象以及它们之间联系的客观世界。在《与极浦书》中,司空图开创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意境审美追求,前一个有形的具体的景象是实境,后一个无形的想象的景象是虚境,将“意境”的内涵从“实境”扩展到了“虚境”。《诗品》描述的由各种意境所构成的各种风格,贯串了意在言外的象外旨趣,如其中所说“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离形得似”等,都要求通过鲜明生动的意象,展现意境与风格。
在《诗品》二十四品中,《含蓄》一品最能体现意境美的本质,因为它揭示了意境中关于由言到象、由象成境、由境体道三个维度的真理,连通了宇宙之道从自然进入人心,从人心进入文字,从文字进入其他人心,最终达到对宇宙之道回归的循环。意境因含蓄而美,没有含蓄就无法产生意境,而其他二十三品都是意境不同风格的表现,并非意境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意境中关于含蓄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是由言到象的问题。象最初是为了解决“言不尽意”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概念,《周易·系辞上》中就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等说法,指出了言表达意的有限性,探索出以象来尽意的表达方式。“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显然也是持“言不尽意”的观点,正如上文所说的,文字的意义是有限的,它无法完全传达出蕴含无限意义的人的所思所想。从言到象的转变反映的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感性思维,古人善于从整体性去感知和把握事物的宇宙性本质,而不擅长以理性的方式分析和解构事物的意义。诗歌创作亦是如此,诗歌必须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诗人心中涌动的最精华的思想情感是统一完整的,它不能用文字或言语进行分割式的表达,而从意义表达的层级来讲,象是高于言的,所以即使我们难以克服文字的有限性,却可以通过文字塑造意象,传达更丰富的意义。
其次,是由象成境的问题。境生象外,虚实相生。司空图提出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等,都明确表示了境不能从象本身得到,应该是把“象外”作为意境得以显现或展开的审美空间。境存于象中,又超于象外,这里的“象外”就是象与象有机组合形成的意象空间,在拓展了感性意象表现力的同时,也赋予了境无限表达的可能性。从虚实的角度来看,象是实的、可感的;而境是虚的,只能体悟不能形容。在《诗品》中有一品为《实境》,其实指的是构成意境的基础是具体实物之境,实境就相当于可视化的象,这也是在谈以象造境的方式。含蓄就是虚实相生的,“如渌满酒,花时返秋”既有表现出来的形象部分,也有看不到的被包蓄的虚的部分,有虚有实才能让读者有灵活的想象空间。《含蓄》的最后两句谈及创作中象的选取问题,实际上也是在谈境的生成问题。由象成境,只有“万取一收”的象才能成就“万取一收”的境。
最后,是由境体道的问题。正如中国山水画是文人体道的方式,诗歌意境也体现了诗人的自然宇宙观和人文观,寄托了诗人游心于宇宙自然的理想。“境”在佛教中本指色、声、香、味、触、法六境,随着佛教吸收儒道思想,在中国逐渐本土化,后来产生的禅宗认为通过日常生活和生命现象即“境”就可以直接参悟宇宙之道。“意境”是在佛教影响下成为诗歌批评术语的,由此“意境”就具有了形而上的“道”的深层意蕴。司空图所说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环中指空虚之处,唯道集虚,因此环中也就是道之所在。《含蓄》一品中的“是有真宰,与之沉浮”,真宰既是指主体的思想主宰,也是指统领主体以及世间万物的真正主宰,即掌握一切造化自然的宇宙之道。这就意味着,意境不仅是创作者对道的体悟和表现的主体空间,它也要求读者能超越有限意象进入到诗歌无限的审美时空之中,从而在感作者所感之时得以领悟意境的最高本体,也就是道。
“诗贵含蓄而恶浅露”,这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原则和审美传统中都是一大特色。诗歌追求的意境也以含蓄为基本要求,以有限精练的形象表达无限丰富的意蕴,实现人心之志与宇宙之道的合一。正是含蓄让意境产生“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美,让诗歌具有了语简而意丰、耐人寻味的艺术感染力,从这一点上讲,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诗品》明确将《含蓄》作为一品,也正是看到了含蓄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司空图对含蓄的审美风格进行的具体阐释,无论是虚实相生,“万取一收”的创作方法,还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审美趣味,都对唐代以后关于意境的诗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