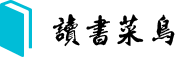《璩家花园》,叶兆言著,译林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
天井姓璩,是长篇小说《璩家花园》(译林出版社2024年出版)里的一个人物。璩家花园是作家叶兆言虚构的南京旧地名,属于“历史文化街区”之类。相传璩家先人做皮货生意,积累了家资,在清朝中叶就有了花园雏形,璩天井的上五代祖宗,中了举,大兴土木,营造起更加辉煌的规模。但是好运不长,在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战乱中,璩家迅速败落,巍峨楼阁随之倒塌,剩下青苔瓦砾一片。应了小说叙事中提到的《桃花扇》里的一曲唱词: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用在民国时期首善之都的金陵石头城历史,倒也恰如其分。到了璩天井的父亲璩民有一代,已经成为时代多余的人,龟缩在破旧老屋苟延残喘。大量外地流民迁徙而来,璩家花园成了各色人员杂居的贫民区,如同电视剧《人世间》里的“光字片”。
璩家花园的居民比“光字片”更加暗淡,也更加复杂。这里也住着教授名流,住着破落户子弟,还有就是工人、家庭主妇、兵痞、流氓、女佣……总称都叫做“小市民”。要说一个城市的小市民的文化性格,总是与这个城市品格密切相关。璩天井的父亲曾是汪伪政权下中央大学的学生,祖上历史有点不清不白,本人又是一个懦弱、苟安的犬儒主义者,但也不乏善良和精明;璩天井的母亲江慕莲是富家千金,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不幸成为国民党军官的遗孀。他们都是时代狂飙下的飞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们也曾渴望跟上时代,两人的相遇,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颇为趋时的“俄语速成班”上,一时苟合后生育了璩天井,随后,江慕莲发疯投江而亡,璩民有勉为其难带着儿子继续苟活——这是小说描写的关于1954年的故事。作家的本章提示是:母亲,天井不知道那些往事。
这个章节里还有许多不忍卒读的细节,暂且不表。1954年是璩天井出生的年份,也是小说叙事时间的第一幕,但作家没有把它设定为第一章。小说开篇已经是1970年,天井16岁——我与璩天井是同龄人,我也生于1954年,1970年那一年我中学毕业,开始走上社会,长大成人。我写过一部少年时代回忆录《1966—1970,暗淡岁月》,最后一节写到1970年上海的中学实行“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分配政策,同学们纷纷去了黑龙江、云南、江西和淮北,“一个班级五十多人树倒猢狲散,大约只有两个人没有被卷入这个洪流,其中一个是我。”我用这个结尾暗示了我由此不自觉地有了疏离于时代潮流的个人意识。但同样是16岁的璩天井却表现得幼稚得多,似乎还停留在1966年我虚岁13岁、身体刚刚发育的阶段。小说第一章讲了两个故事,把天井写得很不堪:一个故事是天井在父亲唆使下去费教授家里偷钱,被女佣李择佳无意撞见,为了逃跑他竟把李择佳撞下楼,不管不顾地逃走了,而李择佳则是他从小被照顾抚养、恩重如母的人;第二个故事写的是天井逃跑后不敢回家,误入破旧老屋祖宗阁,窥探到男女性事,朦胧中似有觉悟。这一章(1970年)作家的提示是:祖宗阁,天井混沌初开。
天井到16岁才“混沌初开”,没有像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只是偷窥而已。从男孩的正常发育而言,似乎有点晚熟。我觉得上述两个故事,应是13岁左右小男孩才会做出的莽撞行为。作家把它安排在天井16岁那年发生,当然是故意的,就是说,天井的身体发育和智力发育都要比常人晚,大约晚了三四年。如小说里转弯抹角地说过的:“他的脑袋瓜里进过水,智力受了影响。”作家塑造的璩天井就是这样一种晚熟、迟钝、有些麻木的慢性子。他与当时所谓的“天兵天将”似的时代骄子恰恰相反,是一个窝囊的“小人物”,不仅总是受到别人欺侮,而且与整个时代潮流拉开了距离。小说第三章才开始写璩天井中学毕业进了工厂,成为一名技术工人,还有了心仪的女孩阿四,算是成人了。那一年是1971年,天井17岁,是初中70届学生。他比我低一届,我是69届初中生,全国上山下乡“一片红”;70届中学生运气好,上海当时实行了“四个面向”分配政策,既有到农村或农场,也有分配到工矿企业。据叶兆言的描写,南京的中学生全部都留在了南京城里。于是天井和他心爱的阿四进了同一个工厂,金陵标准件厂。这个厂说起来是一家集体所有制的街道小厂,居然也有参与接待外国元首齐奥塞斯库的光荣任务,应该不是一家无足轻重的小单位。第三章(1971年)作家的提示是:青工天井和阿四,齐腰赛似裤。进厂当工人和接待外宾,成了他们的成人仪式。
接下来的小说叙事逐渐铺展璩天井的一生道路。长篇小说的叙事模式,在“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中,主要是刻画事件和人物,虽然离不开对时代背景的描写,那主要是写大时代于具体人物命运的影响,并不是有意识地专以时代为描写对象。所谓以“中国近百年史”为长篇小说的主题,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才逐渐形成的一种创作现象,家族题材、农村题材、城镇题材,以及知识分子的成长题材,几乎所有的地方、家族、个人的兴衰史都与时代主题紧扣在一起,不是时代决定人事命运,而是人事的叙事为了见证时代。我觉得世纪之交前后20年,这种倾向越来越成为长篇小说创作的主流。从好的一面来说,以文传史,捍卫历史的真实,这也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自觉的政治意识;从不足的一面来说,过分强调历史既定因素,会减弱文学的主体性,有时候被描写的人物命运沉浮成了阐释历史的说明书。回到《璩家花园》这部小说,自然也未摆脱书写历史的意思,但就璩天井这个人物而言,因为是“小人物”,他的一生轨迹与时代主潮都保持了距离,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再加上随遇而安的性格,他要比别人慢三拍才能感悟到生活步伐的节奏。半个多世纪惊涛骇浪般的时代历程里,他就像河床底下的一粒沙,沉淀在深水之下,寂寞地安稳地度过了一生。
璩天井又是幸福的。尽管他在生活竞争机制里总是被淘汰,成为失败者,但依然是幸福的。虽然小说开篇夸张地描述了他的两件糗事,但他的人生道路并没有延续这样的设定走下去,而是慢慢地走向了反面。第一是他与李择佳的关系,他当初撞倒李择佳自私逃命,但李择佳没有揭露他的偷窃行为,依然包容了他,后来他做了李择佳的女婿,把李择佳当作母亲奉养送终,一时传为佳话;第二是他“混沌初开”后,始终爱恋青梅竹马的阿四姑娘,虽然阿四不怎么爱他,性格也偏豪放,但还是在他的呵护下,维持了长长一生的婚姻关系,获得了真正的幸福。幸福是一种心理指数,在一种无欲则刚的人生境界里,天井对阿四一生追求的痴痴的爱,成为他具有幸福感的保障。纵观小人物璩天井的一生,两个特点保障了他的幸福,一是他生性善良,自始至终坚持了对他人的奉献和爱,还有一个是他有技术,也不是什么身怀绝技,他是一个钳工,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在相对贫困的生活环境里,小人物无权无财,只有高明的技术能力才能解决自身困境,维护做人的尊严。爱与技术,保障了小人物璩天井平安的一生,也是幸福的一生。
璩天井并不是一个现代文学画廊里常见的艺术形象。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小人物”形象是常见的,但是作家的创作态度不太一样。叶兆言没有怀着太复杂的心情来塑造璩天井这个人物,没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没有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怜悯和嘲笑,作家只是带有含泪的微笑和幽默,描绘了他的善良和勤劳,描绘了他默默地为家人做出奉献,也写出了他傻傻的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璩天井从小被父亲领到璩家花园生活成长,到老了依然回到了破旧老屋里安度余年,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天井的一生似无甚变化,还是回到了老地方,走在璩家花园的老旧路上。我们当然可以对这样一种人格投以惋惜和遗憾,但是由此及彼地想一想,我们还有多多少少生活在市井民间的人们,不就是这样沉默地生活着吗?
2024年9月26日于鱼焦了斋
(作者:陈思和,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