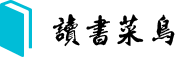通过苏轼关于家、家乡的书写,历代学者大致对苏轼的家观念总结出两种看法:一类学者认为蜀山蜀水才是苏轼最为魂牵梦萦、难舍难分的家园;另一类学者则选择史实中反映的苏氏父子的迁居行为与不归葬行为,为苏轼的家观念翻案。学者朱刚在其著作《苏轼十讲》中另辟蹊径地指出,尽管巴蜀文化符号与其生命历程相始终,但苏轼并没有那么怀恋老家眉山,苏轼的乡土文化观念是相对淡漠的。然而,对于苏轼的家观念,我们既不可简单地凭借其诗词中的家乡、峨眉、蜀地等字眼出现频率高就概括为其对“家”始终怀有深刻的眷恋之情,也不可全凭外界客观因素,将其为避鄙陋、拓新天地的行为推断为乡情淡漠。本文通过结合苏轼仇池唱和中体现的“物观”与苏轼仇池石相关诗歌中体现的家观念,提出历代学者对于苏轼家观念的两种常见论断之外的新的论断的可能性,并由此得出“此心安处是吾乡”为苏轼真正家观念的新阐释。

一、以小观大—仇池石中窥见苏轼与众不同的家观念
(一)何为仇池
想要探求苏轼的家观念,大多数研究者都会选择从苏轼“家”的书写入手,但有时含有“家”和其同义、近义字眼的诗词作品引导性太强,作者对相关字眼有意识地运用往往会无意识地将读者带领到他所期待的解读上去,读者很难再发掘新的解读角度,窥探到作者不经意流露的那些情思和态度。而苏轼的仇池书写,却能够不着一个“家”字,不少一分“归”意。
甘肃西和县有仇池山,绝壁高险,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谓其“高平地方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十分适合隐者避世离俗。乾元二年(759),杜甫以直谏遭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在《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四中写道:“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神鱼人不见,福地语真传。”仇池直通王屋小有洞天,穷途思隐,对于仕途失意的杜甫来说,平田屋舍,白云出岫,不可避免地使他生出长住此间的盼望。
福地藏山,人间换世。北宋元祐六年(1091),千里之外的颍州府衙内,苏轼在一场清梦中也看到了它。元祐七年(1092),他在《次韵和晁无咎学士相迎》中称仇池为他的“归老”之地,“梦中仇池千仞岩,便欲揽我青霞幨。且须还家与妇计,我本归路连西南”;绍圣元年(1094),贬居英州时,他在《过杞赠马梦得》中说“万古仇池穴,归心负雪堂”,意欲通过仇池石走向归隐之所;绍圣二年(1095),他在惠州作《和陶潜读〈山海经〉》,“东坡信畸人,涉世真散材。仇池有归路,罗浮岂徒来”中的“归路”传达了以仇池为家的观念;他在《和陶桃花源(并引)》中写了“高山不难越,浅水何足厉。不知我仇池,高举复几岁”之句,他把仇池比作桃源仙境;他在《次韵高要令刘湜峡山寺见寄》中大赞“仇池九十九,嵩少三十六。天人同一梦,仙凡无两录”,认为登上仇池即可羽化成仙;绍圣四年(1099),贬居琼州时,他在《次前韵寄子由》中直言“泥丸尚一路,所向余皆穷。似闻崆峒西,仇池迎此翁”;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他去世的当年,于北归途中过大庾岭时,他仍有《山坡陀行》言“若有人兮,梦中仇池我归路。此非小有兮,噫乎何以乐此而不去”。以上诗句均可看出苏轼对仇池此山的日思夜念,他毫不掩饰地将仇池认作自己理想中的家园。尽管这些诗作中几乎未出现“家”的相关字眼,但无不借称颂仇池山的瑰丽峭拔与似仙似幻描摹了它与胸中的精神家园、归隐之地的相似性。
然而,元祐七年(1092)后,仇池如此密集地出现在苏轼诗文中,并且承担“精神家园”这一崇高作用的原因,还要追溯到其表弟程之元送来的两块石头上。
(二)何为仇池石
元祐七年(1092)春,程之元赠苏轼一青一白两块奇石,由此开启了苏轼借仇池抒家思的诗歌主题。程之元送来的这对儿岭南英石恰好有意无意地留储了道教的意象寄托,让仍心系梦中偶见的小有洞天、仙家福地的苏轼很自然地想起了颍州的梦与赵令畤的解,并将其取名“仇池石”。《双石》是系列第一首。遍览全诗,这盆石供对苏轼的意义已不完全在于道教福地的象征。诗中“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的想象,有着李白《蜀道难》的影子,“太白”即太乙山,“峨眉”即峨眉峰—仇池本在长安赴蜀的途中。正是这样的地理联系,使出川日久的苏轼想起了眉山故乡。欲往仇池而不可得的苏轼为寄托情思,便将这枚“冈峦迤逦,有穴达于背”的绿色石头命名为“仇池石”。此石有“穴”有“冈”,形貌近似仇池山,以此石为伴,也算离自己的精神家园更近一步。
然而,真正使苏轼对仇池石的重要意义觉醒的事件应是在汴京与藏书极丰,治学亦精的王钦臣闲谈路经仇池的经历时,谓仇池为“可以避世,如桃源也”(《苏东坡全集》)。于苏轼来说,仇池本来只意味着梦中的一场道遁,一如归途上的一个地标,他真正开始对这两块石头另眼相看,正源于与王钦臣闲谈间这一笔无意的回扫。经历赵令畤以梦解道、程之元千里转运、扬州和陶思归、王钦臣喻为桃源,更兼置庭、汲水、埋盆、换盆、缀石种种劳作设计,仇池石之于苏轼,早已不只是一件可以物易的清玩之物,它近乎是东坡躯壳的一部分外化:他肉身不得自由时,则不妨任灵魂出入其中,以石中孔穴,涵养自己求而不得的归梦。
对于常人来说,家是真实存在的、唯一的、固定的、具象的,是“身之所安”之地,所以人们不愿意客死他乡、终希望衣锦还乡。家山,故乡,是不可替代的。哪怕是长久生活居留的地方被称为第二故乡,心中还会保留那个拥有自己属性特征的第一故乡。苏轼却不惮于打破这种单一固化的家观念:心安即是家所在,“此心安处是吾乡”。
围绕苏轼“家”的书写,学者朱刚在《苏轼十讲》中曾指出,屡见于东坡笔下的“无家”之说,与到处迁易、随处认同的“家”是可以被统一起来的,“以无何有之乡为家”,就是既无固定之“家”,又处处是“家”。但既然苏轼笔下“何以为家”的概念被进行了两极分化的界定,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二者混为一谈。因为这种书写的表象之下隐含着:不轻易以一地为家,也不轻易界定家一定是具象的房屋宅院的意义,因而表现在文字上是“无家之说”。但实际上,在仇池石的相关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在广袤的人生中寻觅的精神家园,已经与他因“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记游松风亭》)情绪主导而随处选择的“落脚点—家”之间,划上了十分清晰的界限。从生命境界与心灵归属上看,苏轼注重精神家园构建,注重“心闲”,他认为安顿心灵的所在才能称得上家园,不论这个所在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可以是寸田尺宅,也可以是盆石世界。
人生如寄,家于苏轼更像是一种寄寓,无论何地何物,只要拥有一份能给诗人带来归属的愉悦感,能让他身心舒畅、有所寄托的,都可以幻化为无形的家,收容这个饱经宦海浮沉、命途多舛的浪子。于是,面对着确实寄托了苏轼家的情感与归隐之思的仇池石,苏轼与常人有所不同的家观念开始崭露头角。
二、不滞于物—仇池唱和中揭示自相矛盾的物观
除却一代文豪的名号,苏轼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和慧眼如炬的鉴藏家,他的藏品与他内心的世界遥相呼应,因此,所藏之物便成为他个人内在精神的寄托和心迹的外化表现。作为“赏石大师”,苏轼不仅积极参与“赏石”这项审美活动,也从中归纳出了自己的一套“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的物观。
熙宁十年(1077)仲夏,苏轼在为驸马王诜私人藏画楼“宝绘堂”所作的《宝绘堂记》一文中提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与物相交、寄情于斯,同时却不抱占有或永远拥有的企图,才是苏轼所期望的理想精神境界。对世间万物皆是如此,对家也尤其如是。然而,苏轼成熟圆满的物观在遇到与家相关的仇池石时却分化瓦解了。研究宋代文学的美国学者艾朗诺曾说,苏轼诗文中常常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超脱”,也就是说,“不让自己太执着于物、对物的占有欲太强”。但问题在于这种对“超脱”的执着常常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至少对于这对儿石头,苏轼非常留意于“得”。
元祐七年(1092),程之元送来双石不久,王诜便看上了这对儿奇石。王诜,字晋卿,是苏轼的好友,常与苏轼一同舞文弄墨,共享赏心乐事。苏轼用《仆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意在于夺,仆不敢不借,然以此诗先之》这首五言诗回应王诜之意并道出内情。全诗先描摹石头的外形“秀色如蛾绿”“宛转陵峦足”,再交代石头的来历,石头来自广东,并非甘肃仇池山;接着写自己对待双石的方式,以朝鲜进贡大铜盆贮之,又用蓬莱仙境的登州海石做点缀;最后写对仇池石的珍视与恋恋不舍,诫王诜“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至此,苏轼对仇池石的恋物之情已经昭然若揭。《双石》和这首拒绝诗果不其然引起众友人的关注与唱和,钱勰、王钦臣、蒋之奇连连次其韵为诗,一是想替这桩公案“解围”,也有因为苏轼自相矛盾的言行而“看热闹”的成分在。几人和诗现已不可考,但大体可知内容为对是否应该“借观”仇池石的说明。于是,苏轼又依前韵回复《王晋卿示诗欲夺海石钱穆父王仲至蒋颖叔皆次》一诗,该诗借司马相如的典故诉说了苏轼以仇池石为家园的心情。诗中提到的“眉绿”,与第一首夺石诗中的“蛾绿”相近,处处都回扣着第一首唱和诗中流露的以此石为寄寓的心意。此诗中苏轼虽“大度”表示同意借观,但要以韩干的两幅画马名作作为交换条件。王诜爱画成痴,自然不肯外借如此珍贵的名作。苏轼对此是很清楚的,他的目的就是让王诜知难而退,如此苦心,可见苏轼爱石之甚。正在二人僵持不下之时,又有诗友献计,有人主张画石都弃,有人主张画石兼得,于是苏轼“仇池唱和”的第三首诗《轼欲以石易画,晋卿难之,穆父欲兼取二物,颖叔欲焚画碎石,乃复次前韵,并解二诗之意》应运而生。在此诗中,苏轼套用了“明镜无台”与“定心无物”的偈,意在借“行禅坐卧皆是佛,不必拘泥于一定形式”的禅宗道理劝告王诜莫要执求物象,也莫要执求于空,要从外界的迷乱欲望中返归到自我清净的内心。至此,苏轼以“身外之物不可执着”的观念结束了关于仇池石“借观”与否的唱和诗作。于是,仇池唱和就这样极具讽刺意味地展现了苏轼自相矛盾的物观:一面劝王诜要“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大谈自己年轻时迷恋于物,现已幡然醒悟“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宝绘堂记》)的心态,直言“盆山不可隐,画马无由牧”;一面又找借口、提要求逃避“借观”,敦促王诜尽快把仇石还给他。
从行动上看,苏轼对仇池石的眷恋与《宝绘堂记》以及仇池唱和中显露的物观似乎背道而驰。因此,这场关于仇池石的“公案”开始被许多学者解释为苏轼口是心非的占有欲—毕竟他曾在诗文中那么多次强调造物无尽,告诫朋友不能“留意于物”,此时却用尽浑身解数来捍卫自己的物权,几乎放弃了一个文人应有的体面。然而,真正明白仇池石对苏轼的意义的人则能领会,苏轼对仇池石的守护,实则正在于他对心,而非对物的看重。苏轼的喜欢,通常只流于随喜,他看重的并不是对物的拥有,而是此物能尽多大程度使心灵得到归宿。也就是说,看似仇池石凭借本身的美感特质获得苏轼的青睐,但其实苏轼的喜爱更多地来自超越其外在形态的因素,即主体与客体之间内在精神的契合。苏轼借仇池石寄托家山之思,它仿佛是家的载体,承载着苏轼对心灵避风港与俗世休闲处的所有情思。见其石即似见到那如同峨眉一样充满安全感与归属感的家山,苏轼的心灵因对仇池石的吟咏而获得无比舒适的、满足的归宿。
三、“此心安处是吾乡”
对能够使他“心安”的精神栖息地—“家”的执着追求,是苏轼面对“家”的象征物—仇池石时乱了阵脚、失了方寸的主要原因。对于家,苏轼从未追求“实在的故乡”与“真实的返乡”,只是呼唤着抽象的精神家园。作为心灵桃源的“家”应该只限于心中所持有的那个抽象概念,而非真正的“家”本体,即“此心安处是吾乡”;而当需要一物寄托具体的家的情思时,仅靠书、画、诗词等抽象之物则不能满足。正是这种“不滞于物”而“侧重于心”的物观态度,造就了苏轼与众不同而又平和旷达的家观念,让如微缩景观一样的仇池石作为具象的“家”的替代物与归隐之思的精神寄托,当仁不让地成为苏轼后半生中不断歌咏、不愿出借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