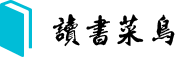作家亦舒,1946年9月25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镇海,五岁时定居中国香港。亦舒塑造了很多成功的女性角色,如前些年爆火的《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君。亦舒具有浓烈的女性意识,她通过笔下的故事,劝告广大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身为女性不应该过度依赖他人,尤其是一向处于家庭地位主位的男性,要利用好自己的武器,为自己谋生存,不仅要在自身精神意识上独立,更要在物质金钱上独立,在种种方面上都要独立。在《喜宝》中,亦舒为喜宝提供过各种各样的选择,但是在面临人生选择的岔道口处,喜宝仍然选择了一条看似不能回头的不归路,并且与自己当初的设想背道而驰,这也是现代女性的生存问题的缩影。如同易卜生“社会问题剧”一样,亦舒只提出问题,却没有提出解决的良方,或许亦舒也并没有解决的良方。所以,借喜宝的经历,亦舒展示了她对于现实问题的考量以及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和希望。

一、对于“女性经济困境”问题的重新提问
喜宝曾经说“如果没有爱,很多钱也是好的”,这样看似物质的言语,其实隐藏在背后的是一种令人怜惜的落寞。通过对于小说的阅读理解,我们发现《喜宝》中无论是主人公喜宝还是喜宝的妈妈,都对于金钱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喜宝没有钱交房租,没有钱交学费,只能依靠自己的男友韩国泰为自己提供学费;为了谋生,喜宝妈妈被迫改嫁移居澳洲。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金钱压力是一座移不动的大山。生存的胁迫用金钱时时刻刻捆绑着喜宝,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抓住喜宝,为了自己能够度日,能够获得一个令人羡慕的学位以便自己可以不至于走向一种繁忙、焦虑、贫穷的家庭主妇生活,所以喜宝只能用自己的青春作为筹码去换取男友韩国泰的经济援助,在她看来,爱情也不过是可供交换的一个物品,连她自己都说:“韩国泰,你完全说得对。你不知道我的忧虑有多重,这些年来我忍受过什么。你有什么好气的?不错你做了我的踏脚石,但是你损失过什么?你难道没有得到你需要的一切?”不错,在这场爱情里,喜宝也只不过是用自己的青春美貌去换取男友的金钱,以及自己生存的必需品。两人之间的爱情在喜宝看来就是一场交易,只是出于生存问题而进行的一场交换。在亦舒看来,物质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女性在生存问题面前只能不断出卖自己的灵魂与肉体,这似乎是一道解不开的谜题。
“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现代香港社会,在商品至上、消费至上的高速运转的殖民地现代都市,女性在金钱与情感间如何选择。”(孙诣芳《香港的情与爱—评亦舒小说〈喜宝〉》)喜宝作为世界名校剑桥的学生,一直为自己的高学历感到自豪,并且认为自己也只有这个高学历可以拿得出手来,在面对勖家的富贵满堂时,喜宝没有耀眼的舞裙和夺目的珠宝,她认为自己也只有这个剑桥高才生学历能说得出。她以为,从剑桥获得的这一纸文凭,就可以为自己走向一个理想化尤其是不需要为金钱担忧的生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喜宝又担心一旦失去这些东西,她又要面临回到香港,到写字楼里去打字,过着一个普通上班族的生活,所以她为了自己的理想生活,必须面对来自金钱的压力。因此,当她面对勖存姿的“金钱”的邀请后,她还是决定放下自己的尊严。虽然她心里仍然有许多不甘,但是当她看见抽屉里永远拿不完的纸币时,她十分心动。喜宝金钱的欲望终于被得到满足,她终于有一种再也不需要为金钱担忧的快感,她沉浸在这“便利”的捷径中,她说“我不介意出卖我的青春。青春不卖也是会过的”。喜宝用自己的青春和尊严,再一次为自己换取了金钱,与其说喜宝是为了自己的学历而选择勖存姿,不如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金钱的欲望而选择的勖存姿,但喜宝也没有办法,她在香港可以说是孤立无援,她在自己的生活里更是无人帮衬,几乎相当于没有父母也没有经济来源,在金钱面前,喜宝必须退让,进行这场“色情”交易。在这场游戏里,亦舒直接指出,要想获得女性权利和地位,只有获得经济独立才能有资格获得基础性的地位,“金钱”成了理想生活的代名词,只有大量的充足的金钱,才能保证女性获得独立的基本权利,但是“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韩昀《〈喜宝〉:女性理想的路径与歧途》)。
“作为女性,喜宝走上也只能走向为金钱卖掉自由的这条路。亦舒用女性自我审视的方式对娜拉问题进行再追问。”(韩昀《〈喜宝〉:女性理想的路径与歧途》)她让生活在20世纪年代末香港的喜宝走出家门。在“女性经济困境”下,亦舒一次又一次向喜宝发出提问,但喜宝自知若是只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仅不能完成学业,更不能生存下去,她只有依附于男人才能解决问题,喜宝找到的这条路,放弃了自我,最终又走向了女性这么多年以来走的一条老路,这也暗示了亦舒也并未找到喜宝的正确的出路。依附男人、委身于人似乎是女性最方便、最快获得一些机会的途径,即使是在一个物欲横流,机会多,开放度、包容度、繁荣度都很超前的香港,女性经济困境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她们依旧要被男耕女织的传统观念束缚,被女性传统定位所限制,她们依旧走上了一条与自己理想背离的路,她们依旧是一个“残缺的人”。
二、女性灵与肉在现实中的抉择
在书中,毋庸置疑的是,亦舒是希望喜宝走向一个理想化的独立女性人生的。在亦舒的笔下,喜宝拥有一切“偶像剧女主”的配置,她拥有令人羡慕的学历,凭一己之力考上剑桥的圣三一学院学习法律;她极富有人格魅力,长相清秀而且身材好。这样的人设令人羡慕,并且已经达到了可以非常容易走向成功人生的要求,只要喜宝保持一颗不要堕落的心灵,在喜宝面前一条优秀职业女性的道路将会慢慢铺开。但正是这样优越的“女性设定”更容易导致喜宝为了保持这些条件而走向一条反方向的“不归路”。这样一条路走下去需要大量的精力和金钱,需要很多付出,走投无路的喜宝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困境,这样的她用自己唯一可以利用的青春作为筹码,去换取韩国泰的经济支撑,或去换取勖存姿的财富。如果说喜宝和韩国泰之间或许还有一些平等的、出于爱情的成分,那和勖存姿的这份交易中,更多的是一种不平等的协议。喜宝将自己的灵魂最终彻底出卖,又因为这份“交易”失去了肉体的自由,也失去了精神的自由,最后完完全全沉浸在勖存姿的世界里,把自己完完全全当作是勖存姿的“人”,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她在最后放弃了自己的剑桥学历,认为即使自己获得这样的学历,也达不到现在的生活质量。所以,她将自己完完全全沉浸在勖存姿的金钱世界里,甚至最后还爱上了勖存姿。这对于喜宝来说是一个悲剧吗?千万别忘了喜宝的身份背景,她自小父母离异,又出国留学,妈妈改嫁后,她在香港甚至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只有一个还有一个月到期的出租屋。这种漂泊无定的生活,让她十分渴望拥有一份安全感,有一份像“家”的归属感,这是她的灵魂的本质缺陷。她的愿望是“希望得到很多的爱”。你可以用金钱买到很多东西,但是唯独买不到一份“爱”。当她一开始签订这份“契约”的时候,她的内心也并没有很多感情,只是把它当作是她的一份工作。但是,勖存姿不仅为她提供了她极度需要的金钱,更为她提供了一份来自“家人的爱”。她仿佛“久旱逢甘霖”,这份“爱”在她看来是非常珍贵的,她逐渐投入到了勖存姿的生活中,他说什么她就听什么,她又回到了传统的“家庭模式”中,“男主外,女主内”,勖存姿的一切成了她的一切,她不自觉地把自己带入“勖存姿的人”这个角色,这就意味着喜宝的精神主体不再是属于她自己,她的灵魂就被永远地烙上了“勖存姿”的印记。
喜宝的灵与肉在面临现实抉择时,不得不向现实屈服,不得不向金钱低头,即使是喜宝一开始只是设想让勖存姿成为自己取得学位的梯子,自己只是他的“员工”,等到她取得文凭后便离他而去。但是,勖存姿的金钱和魅力以及那份“爱”让她不知不觉中就忘记了自我。其实灵与肉本身自为一体,不可能久久分离,当她选择肉体背叛自己时,灵魂也就会不自觉地将她找回。喜宝拥有的那一个梦,一个实现独立的梦,一个不过传统女性生活的梦,也就不自觉地破灭了。亦舒想要我们思考,在书写女性命运时,我们不能忽略这个残酷的现实,也正因如此,我们也需要正视女性在现实中,所面临的内心理想追求与现实因素相矛盾时的两难处境。《喜宝》并没有提出获得财富和独立灵魂的方案,反而续写了一种女性不断陷入其中的重复,这恰恰是在思考女性命运时需要我们重视的。它展现的正是我们当下需要面对,不容忽视的一种现实困境。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发现了女性在追求理想时,时常陷入救赎与放弃的两难抉择之中。
三、新“喜宝式”悲剧的悖论
在喜宝通往人生的路途中,她似乎总是在一条危险的悬崖边上探索。亦舒将喜宝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并意图探究以喜宝为特殊代表的女性,是否能“绝处逢生”。但是面对勖存姿的金钱的诱惑,喜宝试图反抗,并且逃离勖的羽翼走入社会,但是金钱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不劳而获并且能够享受到比公主还公主的待遇让不仅是喜宝,甚至是社会上任何一个人都会为之心动。有钱的人可以享受社会的高级待遇,可以拥有顶级的社会配置,这不就是喜宝追求学历的最高理想结果吗?那喜宝又何须去劳累自己,去争一纸文凭,甚至最后获得这文凭,也并不会使自己过上比勖存姿提供的生活更优越的生活,那奋斗意义何在?这似乎也是一个难以解答的命题。亦舒在这里更是对喜宝的命运发出了深思。
女性问题自兴起以来,无论是“娜拉走后会怎样”的悲剧,还是“子君式”的悲剧,还是“喜宝式”悲剧,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在重复一个怪圈,在一个死环里不断绕圈,不能解答。这些高知女性都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青春色彩,或怀有美好的理想,或对家国怀有大志,她们正在社会里翩翩起舞,但她们却总是会堕入“命运的怪圈”,总会在涉及爱情或者是金钱时不自觉地与男性的灵魂纠缠,总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会诱使女性不自觉地成为爱情的附属、男性的附庸。娜拉的出路是什么,子君的惨死又留下了什么,喜宝的悲剧又该当作何评?
亦舒在结尾处留下一句“勖存姿的故事是完了,但姜喜宝的故事可长着呢”这样一句令人深思的话,看似只是姜喜宝个人的结局,实际是姜喜宝面对这样纸醉金迷的生活对自己理想的彻底抛弃。不仅仅是姜喜宝的故事没有结束,更是亦舒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和无可奈何,一代又一代,会有无数个姜喜宝在重新走一遍这样的路,在一次次对于女性的问题的不了了之中一次次重复命运的悲剧,这是否意味走到了“喜宝式”悲剧的悖论中,女性的独立和解放问题无法解决,甚至是束手无策,始终在无止境地重复。亦舒在现代社会中对于女性问题提出了无数可能性,却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她寄希望于喜宝,又在展示女性通往独立自由和解放过程中出现的悖论,她希望未来有无数的新“喜宝”能够走出“怪圈”,打破“悖论”,将自己的理想妥善保存,将自己的灵与肉仔细安放,走出一条新路,而不是不断重复着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