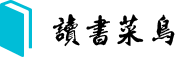《我终于读完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文学体验三十讲》,苗炜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
内容简介:
“到我这个年纪,发觉自己花了三四十年读小说,也会有点儿茫然,好像在虚构的世界里停留得太久了。阅读如同一场游荡,我想留下点儿记录。”
在这本书中,苗师傅谈同理心与二手情绪,坦承对弗里达、伍尔夫、普拉斯等女性艺术家她身之痛苦的共情;谈命运的无常,回顾本雅明、艾略特、普鲁斯特的坎坷人生;谈如何努力阅读“难读的”名著,如中英对照地读《尤利西斯》,也终于读完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谈那些“不是让你亲近的”伟大作家;谈空间的诗学,描述家带给我们的庇护感;谈诗性正义,试图厘清面对人道主义灾难时,普通人应该怎么做;还结合原著,解读现代电影经典,如《肖申克的救赎》《冷血》《飞越疯人院》……“尘世之爱不能永存,所以要扩大自己的感受……我们的爱总会延展出去,画一个很大很大的半径,激发出无限的情感与思绪。文学世界总有东西会漫出我们的现实存在。”
作者简介:
苗炜,1968年生,小说家。《三联生活周刊》编辑。已出版作品《文学体验三十讲》《给大壮的信》《烟及巧克力及伤心故事》《星期天早上的远足》《寡人有疾》《面包会有的》《让我去那花花世界》等。
目录:
前 言 尘世之爱不能永存
第一讲 同理心的文学测试
第二讲 一张脸的自传
第三讲 女性痛苦的共通性
第四讲 你不加点儿个人体悟吗?
第五讲 乱七八糟的二手情绪
第六讲 情绪与书写
第七讲 歇斯底里的姐姐
第八讲 都是俗世的牧师
第九讲 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第十讲 什么叫诗性的
第十一讲 飞越疯人院
第十二讲 精神病电影列表
第十三讲 《肖申克的救赎》和《善的脆弱性》
第十四讲 《肖申克的救赎》与野蛮
第十五讲 我的人性只够怜悯我自己
第十六讲 被烧得那么彻底
第十七讲 我终于读完了《卡拉马佐夫兄弟》
第十八讲 伟大作家不是让你亲近的
第十九讲 你真的要读《尤利西斯》吗
第二十讲 我们还需要鸡蛋
第二十一讲 空间的诗学
第二十二讲 被摧毁的阿卡迪亚
第二十三讲 和家人相处时间的长短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忍耐力第二十四讲 最平常的恐怖故事
第二十五讲 阅读是一件很私人的事
第二十六讲 你当向往辽阔之地
第二十七讲 德累斯顿二三人
第二十八讲 集中营简史
第二十九讲 诗性正义
第三十讲 让本雅明这样的人活下去
附 录 本书各讲提及图书和电影版本
精彩评论:
苗老师讲课,几乎可以直接兑换成肉身经验。愉悦,是他的最低纲领,也是最高纲领,一如罗兰·巴特的文学守则。
——毛尖(作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苗师傅的文字跟他真身一样,读起来像个慢性子,引经据典讲讲里面的道道,偶尔冒出点坏水。
——王小峰(作家、《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笔)不掉书袋,不抖机灵,踏实地把人讲哭了,这是本领所在。此书不算文学批评,此书有关个人如何通过文学与自己和世界和解,关乎生命。
——豆瓣读者Malingcat评《文学体验三十讲》
为苗炜美妙的分寸感喜而开笑,这是一种带有温度的叙述,不卑不亢的诚恳,浓而不烈的燃情。这本书可以理解为最大诚意的入门向导,最大限度的共鸣尝试,以及成书于艰难时世的留给世界的礼物。
——豆瓣读者神威评《文学体验三十讲》
在线试读:
这篇前言,我想说三个意思,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起承转合,索性硬生生地分成三段吧。
想象一下,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这一天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北京城里应该有了过年的气氛,或许有零星的爆竹声响起。在西城的小羊圈胡同,也就是现在的新街口南大街小杨家胡同,有一位四十一岁的产妇生下了她的第八个孩子,取名庆春。这一家是旗人,汉姓是舒,舒庆春就是老舍的本名。六十多年过去。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新街口豁口西北边的太平湖公园,现在的北京地铁太平湖车辆段,当时是有两片水面的小公园,老舍走到这里,在水边一直坐到入夜。第二天早上,晨练的市民发现水面上漂浮着一具尸体。这就是老舍的结局。
从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傍晚出生,到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夜辞世,老舍活了六十七岁。出生的地点和死亡的地点,相距只有几里地,出租车起步价之内就能到。这两个地方都在北京的西北角。扩大一点儿范围,从阜成门到西四,到西安门大街,到景山、鼓楼、德胜门、西直门,再回到阜成门,这就是北京老城的西北部分,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在这片区域。这片区域也正是清末正红旗和镶黄旗的驻地,老舍的爸爸就是正红旗下的一个士兵。
再想象一下,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黎明时分的圣彼得堡。涅瓦河上的冰开始破裂,春天来了,但这个早上的气温还是在零度以下。沿涅瓦河向南,经过枢密院广场,能看到彼得大帝的铜像,再往前走就是大海街,大海街四十七号是两层楼,佛罗伦萨式的殿宇风格,二楼有一个房间亮着灯,这是个大户人家,姓纳博科夫,几代人都在朝中做官。在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这家人的媳妇叶莲娜产下一名健康的婴儿,取名叫弗拉基米尔。
老舍和纳博科夫,这两人的生日差了几十天。这两人有什么关系吗?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老舍出身贫寒,靠人接济才上了小学。纳博科夫生在富贵人家,家里的图书馆藏书上万册。老舍到二十岁当了小学教师,开始写作。纳博科夫一家遇到了“十月革命”,流亡海外,他去了德国,去了英国,后来去了美国。老舍也在英国待过一段时间,写了《二马》,后来回国,在大学教书,在青岛写出一本小说叫《骆驼祥子》。纳博科夫先写诗,后来写小说,他的作品只在俄罗斯流亡者中有点儿影响。不过他在五十六岁那年写出的《洛丽塔》大获成功。
这两个人的生活轨迹没有交集。这两个人只在我这个读者心中有交集。
我最早接触老舍的小说是听董行佶播讲的《骆驼祥子》,每天守在收音机前,听祥子丢了车,牵回了骆驼,祥子攒钱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龙须沟》,看到了《四世同堂》,在剧场里看到《茶馆》,看老舍写文章说,他闭上眼,北京的一切就能在他脑海中浮现,活生生的人就出现,就在他身边说话。老舍所构建的北京对我来说是一个诗性的世界。
有一年,我去瑞士蒙特勒,在皇宫酒店的顶层逗留了几个小时,纳博科夫最后十来年就生活在这个酒店里。从顶层望出去,能看见湖水和雪山。他在《说吧,记忆》中有 这 样 一 段 话:“每当我开始想起我对一个人的爱,我总是习惯性地立刻从我的爱——从我的心,一个人的温柔的核心——开始,到宇宙极其遥远的点之间画一根半径。我必须要让所有的空间和所有的时间都加入到我的感情中,加入到我的尘世之爱中,为的是减弱它的不能永存。”尘世之爱不能永存,所以要扩大自己的感受。这是纳博科夫的写作手法。
再重复一遍,这两个作家没什么关系。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视为潜在的小说来观察,这两个出生日期只差两个月的作家,却像是一个故事中的两个角色:一个坚守在自己的语言中,用最常见的两三千个汉字写作,另一个掌握多种语言,是伟大的文体家;一个不自觉地要靠近权力,另一个相信文人最好处于流亡之中。他们的交会之处是在我这个读者心里,我生在北京,却对北京有一种古怪的乡愁。这乡愁有一点儿是老舍给的,也有一点儿来自纳博科夫,我们的爱总会延展出去,画一个很大很大的半径,激发出无限的情感与思绪。文学世界总有东西会漫出我们的现实存在。
以上是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