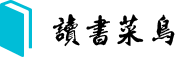《甘苦同食:中国客家乡村的食物、意义与现代性》,[美]欧爱玲著,沈荟 / 周珏 / 王珺彤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
内容简介:
中国已经从三餐不继的困窘年代走到如今食物富足的幸福年代。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农村地区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人与食物的关系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本书作者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凭借在广东梅县月影塘等客家村落长达二十年田野调查积累的丰富记录,探讨食物在中国农村所扮演的角色,为了解当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纵使风云变幻、人世沧桑,“联结性”和“地域感”仍在中国乡村社会发挥着不容小觑的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
哈佛大学博士,现为美国明德学院社会人类学系戈登·舒斯特(Gordon Schuster)讲席教授,广东省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客座教授,曾出版《饮水思源:一个中国乡村的道德话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血汗和麻将:一个海外华人社区的家庭与企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等人类学著作。
目录:
丛书弁言
中文版序
序
译者说明
第一章 中国农村食物的价值
第二章 劳动
第三章 记忆
第四章 交流
第五章 道德
第六章 欢宴
结语 相连的世界
附录A 1949年至改革开放时期梅县的农业生产变化附录B制备节日大餐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编辑推荐:
海外中国研究与世界饮食人类学的前沿佳作
本书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欧爱玲教授对华南客家村落饮食人类学考察的最新成果。 欧爱玲长期“下沉”客家村落进行追踪调研, 对许多中国乡村饮食文化现象有着视角独特的深描,较之普通观察者更能从表象背后解读出更深层次的秩序和价值。
客家饮食、 “老广味道”生动故事的一手采写
本书包含了欧爱玲教授在广东梅县等地大量一手乡土饮食调查资料, 生动反映了几十年来客家、 广东地方饮食的历史嬗变与经典传承。 本书第六章更是将当地土菜之人文表达演绎得淋漓尽致。
华南社会、 客家村落乡愁的“活历史”谱系
本书以饮食为轴线展开, 但最终写作旨趣还是落脚在中国乡村社会上。 翻阅本书, 读者可真切感受到社会变迁(特别是普遍工业化) 带给乡村饮食、 农业社会人情的巨大影响, 触摸到数十年乃至更大时间尺度上华南社会、 客家村落乡愁的“活历史”谱系。 因而,这本“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 听得见乡愁”的著作值得中国读者全面了解。
前言:
中文版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本人著作,我很乐意为中文版作序。
在任何社会中,特别是在快速城市化的社会中,从文化、社会和经济的角度理解食物都至关重要。纵观中国历史,对绝大多数农村人而言,防止饥饿始终是头等大事。食物的生产和交换及其社会用途和文化意义,是农村农民生活的焦点。过去,在应对自然灾害和经济、政治精英的需求之外,他们努力为自己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包括粮食生产的日益工业化和许多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出现了不同的问题。首先,在经济快速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农村丰富的饮食文化能否延续?其次,食品的生产和交换是否仍然是中国农村经济生活以及文化、社会和道德价值观的核心?最后,在中国如此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为什么对农村饮食文化的研究如此重要?由此,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从种植和加工的劳动,到烹饪和宴会的仪式,农村的饮食能教给我们什么呢?反过来,农村的饮食如何适应或影响社会和经济快速转型?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考察了中国东南部一个村庄居民过去和现在的实践及其信仰,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其中的一些问题提供答案,并加深我们对现实问题的理解。作为人类学家,我们不仅通过观察来学习,还通过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幸运。在多次访问的过程中,我被“月影塘”的村民慷慨接受,因为我参加了庄稼收获、乡村宴会、日常用餐、生命仪式以及朋友和亲戚的日常来往活动。在这些方方面面的活动中,食物通常是社会关系的焦点和关键媒介。
最后,我要感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与梅州市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的支持与协助。对参与本书中文版翻译的几位译者,我更要深表感谢,尤其要感谢周云水博士对此书翻译所做的各项协调工作。
在线试读:
每天为家人做饭: 从日常膳食到年节仪式
走进殷照的厨房,就像在阅读月影塘的烹饪历史。殷照祖上是海外华人,他从印度尼西亚回来后建造了一座漂亮的石房子(并非20世纪30年代常见的泥砖房子)。20世纪80年代,月影塘的多数家庭都搬出了老旧的泥砖房,住进新建的房子里。然而,殷照家的老房子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她的厨房里,一口古老的大锅架在砖炉上,下面放着过去人们喜欢用来生火的木头和火种。此外,殷照的厨房和现在多数家庭的厨房一样,燃气、燃气炉样样俱全,只不过她家还用猪粪加工的沼气——邻居用殷照的棚子养了十头猪,殷照则得到沼气作为回报。
殷照厨房里的老灶告诉我们,过去做饭的第一步是收集燃料和水。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村民还在周围的山上砍伐木柴。妇女和女孩们会去流经村庄的河边取水,然后用扁担挑回家。爱玲现在是一名助教,两个孩子还在上大学,她依然记得当时自己比兄弟们干得更多:“我有五个兄弟,所以我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一天要到溪边打好几次水,还要上山去拾柴火煮饭。”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村民开始用煤炭取代木材,也就无须收集木柴烧火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天然气成为首选能源,但并非所有家庭都使用来自猪粪的沼气,很多家庭选择购买燃气。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末期,家家户户开始凿井,去河边取水的人寥寥无几(现在人们喜欢从天然蓄水层中寻找更纯净的水)。
除了炉灶,家家户户的厨房都配有几块很厚的砧板、几把锋利的菜刀、大大小小的炒锅、汤锅和一个电饭煲,这是最低配置。个别家庭还配置了冰箱,但通常只用来储存特殊物品,比如剩饭剩菜,尽管这些剩菜剩饭通常会被放在一边,在下一顿饭被吃掉。有趣的是,与美国家庭不同(冰箱在美国家庭扮演着核心角色),月影塘的村民很少把冰箱放置在厨房里,而是放在别的房间。
在多数农村家庭,内与外的界限并不分明。部分食物制备可以在公共场所进行。比如,村民会把砧板或塑料盆拿到屋外,坐在低矮的塑料凳子上切菜、削皮、冲洗蔬菜。如果邻居来串门,他可能会蹲下来,一边帮忙择菜,一边闲聊。不仅如此,烹饪和进食基本不在同一空间,后者一般在庭院或后院进行。例如,宋玲家通常在庭院旁边的一个封闭区域用餐。那里放着一张圆桌和一摞凳子,吃饭的时候按照人数摆放凳子。庭院还可以充当食物准备的空间,比如村民会在院子里切菜、杀鱼。
当地人在食物准备上的分工与水稻、蔬菜种植一样,都以中老年妇女为主。这两者都涉及家庭的直接供给,都体现了食物的使用价值(即使是购买来的食物,在烹饪环节也会转化成使用价值)。然而,食物烹制与食物种植的分工并非完全一致。与自给农业相比,做饭不完全是女性的责任,而且就分工的代际特征来看,后者的分布更为分散。
例如,在2007年接受调查的35个家庭中,有2/3的家庭由一名或多名妇女掌勺。有4个家庭的烹饪工作全权由父亲或祖父负责,还有4个家庭是配偶一起做饭。有些家庭的分工比较复杂,比如父母、儿子和儿媳一块参与,有时孙女也会帮忙。
因此,尽管女性负责做饭是当地的“默认”选项,但事实上分工并非如此单一。此外,烹饪和耕田的差异也体现在其他方面。村民们会告诫后代通过勤奋读书摆脱耕田的命运,但为家人做饭却没有这样的负面含义。事实上,许多年轻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掌握了基本的烹饪技能。比如,我采访过一位年轻女性,她在当地电视台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但仍然和父母住在村子里。关于学做饭,她是这样说的:“我们主要是从爷爷奶奶那里学的做饭。一般都是女孩学做饭,当然有些男孩也学。父母工作忙,所以一直都是祖父母教我们。如果没有祖父母,我们就帮父母一块做饭。如果住在城市,不和父母一起住,那你可能要买一本食谱学习做饭。”
第一章提到的每顿饭的“配置”对于烹饪也是至关重要的。如前所述,在中式饮食中,某种饭与肉或蔬菜的搭配具有悠久的历史,也是客家日常膳食的框架。与美国的三明治或冷餐不同,客家人习惯将食材放在一起煮熟或加热(这也是冰箱通常被放在其他房间角落的一个原因)。如果家庭规模较小,那么饭菜也会相对简单,但无论如何,饭和菜缺一不可。例如,苗丽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她的女儿已经出嫁,儿子仍单身。她现在和成年的儿子住在一起。家里种稻、种菜、养鸡,还种了几棵柚子树。她和儿子吃的菜都是自家菜园种的,所以只有肉需要买来吃。苗莉吃得很简单,通常是米饭搭配一荤一素,或者她会做一道荤素一起炒的菜,配米饭和汤吃。不论如何,每顿饭基本都是主食搭配荤素菜。
我曾和大约20名六年级的孩子进行了一次短途的一日游,当时我了解到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做饭。我是那趟旅行中唯一的成年人。那一天,我们骑自行车去了一座佛教寺庙(大约用时一个小时),然后徒步爬上一座小山的山顶。到达后,学生们打开背包,拿出锅碗瓢盆、食用油、炊具和基本食材——切碎的肉和蔬菜、酱油,还有鱼露。然后他们开始生火,用饭锅和炒锅做午餐。我相信如果是在美国,孩子们会从背包里拿出三明治和袋装薯片。
年轻人也会在农历新年等节日帮忙做饭。就像一年中只有特定的时间才收获稻谷一样,老年妇女们会组织年轻的家庭成员一同制作食物,为庆祝活动做准备。例如,他们会制作炸米粄或者蒸米粄,有甜口的、咸口的,都是用糯米粉或小麦粉和一些当地的食材制成的。春节期间,人们会在桌子摆上年粄和茶水,招待来访的亲朋好友。不同于平日里的早餐(粥和配菜),发粄是春节期间早餐的亮点——村民喜欢在早餐吃上几块,因为制作好的米粄好几个星期都不会变质,所以只需要重新加热一下即可。
现如今,制作米粄可以促进代际交流。因为年轻力壮的父母基本都外出务工,所以留守的中老年妇女负责为一大家子——儿子、儿媳以及出嫁的女儿们准备新年美食。因此,春节还没到,年长的妇女便早早准备好发粄,分给各个小家庭。
我问宋玲为什么村里人会这么做,她说女儿们太忙,没有时间做这些,但她们又不喜欢县城里卖的煎粄。据宋玲介绍,市场上卖的和手工自制的毫无可比性。前者都是用劣质油做的,不利于消化;后者不仅用料好、口感佳,还能加强宋玲与女儿之间的义务纽带。月影塘的长辈们认为,现在的儿女可能不像过去几代人那样孝顺,所以他们会尽其所能地帮助孩子,以使他们产生一种负债感(第五章将详细讨论这一主题)。
制作煎粄需要好几道工序——和面(需要好几种面糊)、揉面、切片、固形。春节期间,老老少少都在家,所以祖辈经常和孙子孙女(尤其是孙女)一块制作煎粄。由于制作的量比较大,天然气又非常昂贵,所以他们会收集很多木柴,在院子或庭院里支一口大锅,生火蒸煮。
1996年和2007年冬,我恰巧在月影塘。我帮村民们备年货(包括制作煎粄),与他们一同庆贺新春。2007年,距离新年大概还有一周,我去拜访了殷照。当时她正在和两个出嫁的女儿、长子和大儿媳,以及两个正在读大学的孙女一起制作年粄。那一天,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制作了一种油炸芝麻球(当地人叫“煎粄”)。后面几天又制作了好几种年粄。最后一算,她们家一共用了50多斤(67磅)糯米粉,并且有七个家庭参与了制作: 四个已婚子女(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一个已经成家的孙女和殷照自己的两个亲妹妹。殷照自己也留了一些点心,好招待来访的客人。
宋玲也花了几天时间准备年货。她找来了儿媳、孙女和一位邻居(雇佣)帮忙。包力也参加了,但他和的面太稀了,所以宋玲让他“上一边去”!
如果将那些靠做饭谋生的人也计算在内,那么月影塘会烹饪的人群就更壮大了。许多年轻人在县城或者更远的大城市当厨师,返乡后也会主动帮忙做饭。
又如2012年的中秋节,宋玲的儿子燕红为家人精心准备了一顿大餐。燕红做起饭来游刃有余,因为他在广东省的2个大城市——广州和深圳当过十二年的厨师。(那天,他用了不到90分钟就做了一大桌子美食,令人赞叹不已!)我一边观察燕红做饭(妹妹和妈妈帮忙打下手),一边记录了制作家庭大餐的全过程(参见附录B,准备节日大餐)。
当然,尽管那顿中秋团圆饭十分精致、丰盛,但只能算是一顿家庭聚餐,而非一场正式的主宾之宴(下文将详述此类宴会)。那顿饭中唯一的非家族成员是宋玲结拜姐妹的儿子以及他的家人,他们几十年来一直与宋玲和包力密切来往。然而,有趣的是,只有这位非家庭成员带了“像样的”礼物——一大盒香港产的精美月饼。
燕红的妹妹们只带了一些晚餐用的食材,但她们一来就进厨房帮忙做饭。此外,不同于许多正式宴会那样,这顿饭上大家并没有接二连三地敬酒,也没有喝得酩酊大醉——包力只是举起酒杯,简单地祝大家身体健康。
尽管那顿饭的制备十分繁复,但它和种菜、耕田一样仍以家庭为导向。那么正式宴会的烹饪是怎样的呢?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一样,宴会的准备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以往村民会请其他村民前来帮忙准备宴会,并用礼物或传统的红包作为补偿。而现在,村民偏向直接将这项工作外包给专业的餐饮团队,由他们向员工支付工资。尽管宴会的制备逐渐商业化,但并未完全取代早期的烹饪模式,只不过是新增了一种劳动形式而已。
为了更好地分析这种现象,我把宴会视为月影塘人们所说的“食酒”——喝烈酒或白酒。如前所述,这与“食饭”是一组相对的概念。“食饭”的意思是吃米饭,专指日常饮食。此外,宴会在客人身份上也有一定要求——必须包含非直系亲属。一大家子聚在一起用餐被称为“好事”,比如燕红在妹妹和妈妈的帮助下准备的中秋节大餐。但即使他们一块喝了酒,仍不属于“食酒”。同样,农历新年前夕也有一场隆重的家庭聚会,也就是所谓的年夜饭,当地人叫做“团圆饭”。这顿饭旨在家庭团聚,所以名称中用的是“饭”,而不是“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