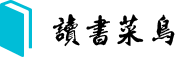《迷人的推理》,[美]约瑟夫·刘易斯·弗伦奇编选,李响林/魏思雯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
内容简介:
《迷人的推理》是美国小说家、编辑、诗人约瑟夫·刘易斯·弗伦奇编选的推理故事集,分为《谜题故事》与《侦探故事》两部分,共收录13位开山派推理大师的16篇精彩故事。
《谜题故事》收录了8篇故事,包括侦探小说的开创者爱伦·坡的《长方形箱子》,此故事里运用的设置悬念的技巧成为了后世的典范;威尔基·柯林斯的《的怪床》呈现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美国19世纪伟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的《胎记》展现了人性的拉扯……《侦探故事》收录了8篇故事,包括侦探小说的开创者爱伦·坡的《失窃的信》;早期幽默侦探故事的威尔基·柯林斯的《自作聪明》;“英国侦探小说之父”柯南·道尔的头篇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短篇小说《波西米亚秘闻》……
作者简介:
约瑟夫·刘易斯·弗伦奇(Joseph Lewis French)。
《纽约时报》评选的传奇编辑,以编选了众多畅销的奇幻、悬疑、推理等类型小说集而闻名,入选英国权威传记参考书《名人录》。
目录:
《谜题故事》
前言
的怪床 ——〔英〕威尔基·柯林斯
迷人的朋友 ——〔英〕威廉·阿彻
胎记 ——〔美〕纳桑尼尔·霍桑
瓦尔迪兹蓝宝石 ——佚名
遗失的房间 ——〔美〕菲茨·詹姆斯·奥布赖恩神秘卡片 ——〔美〕克利夫兰·墨菲特
长方形箱子 ——〔美〕爱伦·坡
希望的折磨 ——〔法〕维利耶·德·伊斯勒·亚当《侦探故事》
前言
失窃的信 ——〔美〕爱伦·坡
可怕的绳子 ——〔美〕玛丽·E.汉肖、托马斯·W.汉肖夫妇苏格兰场的那些事儿 ——〔英〕罗伯特·安德森爵士自作聪明 ——〔英〕威尔基·柯林斯
黑手 ——〔英〕亚瑟·B.瑞福
安全火柴 ——〔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波西米亚秘闻 ——〔英〕柯南·道尔
消失的第十三页 ——〔美〕安娜·凯瑟琳·格林
前言:
《谜题故事》前言
最近,一位杰出的美国小说家对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思维上的锻炼。”现在,我推荐给大家的推理故事就是对我们思维的一种训练。当书本前的你跟随着一系列的事实进行推理时,你的大脑会得到充分的锻炼,也是在经历一次剧烈的思维运动。但是推理小说的价值不能仅仅局限在读者之中,作为写作水平的衡量标准,它理应在短篇小说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人们对于推理故事的需求从未像现在这般强烈。当下,文学潮流瞬息万变,世界局势也变得十分复杂。人类对于世界的探索已经足够充分,几乎没有什么神秘可言。而神秘感是读者的兴趣所在,作者必须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因此,一方面,我们不断探寻人类社会的奇闻逸事;另一方面,我们着眼于超自然现象推理小说,以期给读者带来一些新鲜的刺激感。
谜题故事是推理小说中最为淳朴的文学形式。它可能包含一定的超自然元素,带有一丝神秘主义的色彩,但它的动机和揭示的主题必然是唯物主义的,与现实世界相关。从这种角度来讲,谜题故事与侦探小说非常类似。
一个好的谜题故事的主题要非常接地气,叙事方式要简单直接。如在《长方形箱子》中,爱伦·坡这位伟大的现代大师的天才之处就可见一斑,我们也可从中看到这一类型文学的雏形。本书精选的谜题故事系列内容广泛,是文学作品榜上的首选。
《侦探故事》前言
现代侦探小说之父——爱伦·坡是一位美国作家。他的许多作品,诸如《失窃的信》《莫格街凶杀案》等,至今都无他作可匹敌。
在众多侦探角色中,要数夏洛克·福尔摩斯更为人所知。而以夏洛克·福尔摩斯为代表的诸多侦探角色皆以奥古斯特·杜宾为原型。要知道,当爱伦·坡创作出杜宾时,连美国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其在未来的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的侦探小说流派完全建立在爱伦·坡的作品风格之上,英国的柯南·道尔则借鉴了爱伦·坡和作家的风格,现代的美国小说家们又借鉴了和英国作家的作品。然而,时至今日,纵观侦探小说,能够创作具有“严谨想象力”的侦探角色的作家仍是少数,奥古斯特·杜宾算一个;狄更斯如果再晚几天辞世,也许能创作出另一个——他的最后一部作品《艾德温·德鲁德之谜》成了永远的未解之谜。有一位仍在世的著名作家曾说过,如果狄更斯的寿命再长一点儿,他或许能成为除爱伦·坡之外的秀的侦探小说家。
已问世的侦探小说大多基于两种推理方法:分析和演绎。前者以爱伦·坡的作品为代表,后者以柯南·道尔的作品为代表。现今的部分侦探小说在创作时关注并应用了最新的科学发现,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该领域的代表人物是亚瑟·B.瑞福,他也是第一位用这种方式创作侦探小说的作家。亚瑟·B.瑞福是一位美国作家,本侦探小说集就收录了他的作品《黑手》。《黑手》试图在其有限的篇幅中,描画出刑侦手段的发展过程。
在线试读:
失窃的信
〔美〕爱伦·坡
《失窃的信》导读
1.《失窃的信》的作者是美国作家、诗人、编辑、文学家爱伦·坡(1809—1849),他以诗歌和短篇小说(尤其是神秘小说和小说)而闻名世界,被认为是侦探小说的开创者,也是发展科幻小说类型的重要贡献者。
2.柯南·道尔说:“爱伦·坡的每部侦探小说都是整个文学流派发展的根源……在他为侦探小说注入生命之前,侦探小说在哪里?”
3.《失窃的信》是爱伦·坡以虚构的C.奥古斯特·杜宾为主角的三篇侦探小说中的第三篇,另外两部是《莫格街凶杀案》和《玛丽·罗热疑案》。这三篇小说被认为是现代侦探故事重要的先驱。
4.《失窃的信》于1844年首次发表于文学年鉴《礼物:圣诞、新年和生日礼物》。该小说很快被众多期刊和报纸转载,1845年被收入《埃德加·爱伦·坡故事集》中。
5.《失窃的信》发表前,爱伦·坡在写给美国诗人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的信中说:“它也许是我最好的推理小说。”
6.爱伦·坡在故事开篇引用了所谓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话,但这句话并未在已知的塞涅卡作品中出现,而是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诗人彼特拉克的文集《论命运的补救之方》。爱伦·坡可能是从英国小说家塞缪尔·沃伦的小说《一年一万》中引用了这句话。
智慧忌惮过度聪明。
——塞涅卡
那是十九世纪秋天的一个傍晚,天色刚暗,微风阵阵。在巴黎圣日曼街区杜诺街三十三号三楼的一间狭小的书房里,我的朋友,C.奥古斯特·杜宾正和我一样,一边抽着海泡石烟斗,一边打坐冥想。我们已经像这样享受了一个小时,房间内寂然无声,宁静而肃穆。若此时有人透过窗户看上一眼,大概会觉得屋内的两人正心无旁骛地沉浸于眼前缭绕的烟气。不过,至少我还在琢磨刚刚谈论的话题——“莫格街凶杀案”和“玛丽·罗热疑案”。所以,当我们的老朋友——巴黎警察局局长G先生,他碰巧在此刻破门而入时,我竟隐隐有些期待。
多年未见的老友登门拜访,我们自然是十分欢迎的,虽说他有时并不讨人喜欢,但多数时候是位有趣的朋友。局长说,他有一桩很棘手的案子想要讲给我们听,顺便看看杜宾有没有什么建议。杜宾本来已经起身要去点灯,听他这么一说又一屁股坐下,任凭屋内一片黑暗。
“如果这件事需要仔细思考的话,”杜宾解释了没有点灯的原因,“黑暗的环境再合适不过了。”
“你又有了一个古怪的观点。”局长说。在他看来,一切无法理解的事物都是“古怪的”,他的生活也因此被“怪人怪事”团团围住了。
“确实。”杜宾并不否认,递给客人一支烟斗和一把舒适的座椅。
“那么,这个案子有多棘手?”我问道,“该不会比行刺、暗杀还要棘手吧?”
“不会,不是那种事。其实很简单,不是什么大事,本来我们可以自己解决的,但我一想,这么古怪的一件事,杜宾先生可能会感兴趣。”
“很简单但又很古怪的一件事吗?”杜宾说。
“嗯,差不多,但又不完全是这样。唉,被这种小事绊住,我们也很郁闷。”
“也许就是因为事情太简单了,你们才会被绊住的。”我的朋友说。
“净胡说!”局长大笑着回答。
“真相也许显而易见。”杜宾说。
“天哪,这是谁说的?”
“显而易见。”
“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看得出我们的客人被逗笑了,大笑着说:“杜宾啊,你真是长在了我的笑点上!”
“所以,到底是什么案子?”我问。
“啊,这就告诉你们。”局长坐正,深吸一口气说,“我会长话短说,不过在此之前,先说好,这事要保密,如果有别人知道我跟你们讲过,我的职位可就不保了。”
“讲吧。”我说。
“也可以不讲。”杜宾说。
“好吧,事情是这样:一位权贵私下里告诉我,皇宫中遗失了一份重要文件。他知道小偷是谁,因为有人目睹了小偷的偷窃过程,并且可以肯定的是文件还在小偷手里。”
“为什么能这么确定?”杜宾问。
“很好判断,”局长回答,“这份文件的性质很特殊,一旦小偷公开它,必然会引发事端。虽然现在还无事发生,但迟早会出事。”
“能再多说点儿吗?”我说。
“可以,但我可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告诉你们这些的。是这样,文件的持有者可以凭此文件掌握某种极高的权力。”局长像往常一样打着官腔。
“我还是不太明白。”杜宾说。
“还不明白?好吧好吧,某个人——你们先别管是谁——如果他看到了这份文件,就会怀疑有一位权贵背叛了他。文件的持有者可以利用这一点威胁这位权贵,因为他可以毁掉这位权贵的名誉和一切。”
“但是这个威胁,”我反驳说,“建立在小偷知道文件的主人已得知真相的基础上,哪个小偷敢——”
“这个小偷,”局长说,“是D部长。他敢,他什么都敢做,不管合不合规矩。他偷得那叫一个明目张胆啊。我就直说了吧,重要文件其实就是一封信。收信人独自在皇宫的卧室中,正准备读信时,另外一位权贵突然进来了,而她尤其不希望他知道这封信的存在。但是匆忙之中,她没能把信塞进抽屉里,只好随手放在了桌面上。所幸只有信封上的地址露在外面,信的内容还被封在里面,所以没有引起来访者的注意。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D部长也来了。他一眼就注意到了这封信,认出了信上的字迹,还注意到了收信人的窘迫。很明显,他看透了她的秘密。D部长像往常一样匆匆地汇报了一些商业上的事务,然后拿出了一封几乎一模一样的信,假装读了起来,读完,便把它和桌面上原本的那封信放在了一起。然后他又谈论了十五分钟的公务。最后,D部长临走时从桌子上拿走了那封不属于他的信。当然,信的主人目睹了这一切,但某位权贵还站在她的身边,她不敢轻举妄动,只好任由D部长把信换走。”
“那么,”杜宾对我说,“信的主人确实会受到威胁,因为小偷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没错,”局长说,“而且几个月来,小偷已经用他‘偷来的权力’影响了政局,这是十分危险的。信的原主人越来越迫切地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信,但显然又不能光明正大地把信要来。绝望之下,她最终决定将此事委托于我。”
“除了你,”局长的周身缭绕着打着旋儿的烟气,“还有更合适的人选吗?我看没有。”
“您太抬举我了,”杜宾回答,“要是以前听到这样的夸奖,我大概会很开心呢。”
“确实,”我说,“就像您说的,信应该还在D部长的手里。持有信才能获得权柄,所以他不会把信给别人。”
“没错,”局长说,“不然我也不会采取行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搜查D部长的住所,但有个大麻烦,就是搜查工作得瞒着他秘密进行。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得到了警告——让他怀疑我们。”
“可是,”我说,“您应该很擅长这种调查吧,巴黎的警察以前经常这么干。”
“哦,是的,没错,所以我才不至于陷入绝望。D部长的生活习惯也给我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他经常整晚不回家,仆人不多,住得很远,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那不勒斯人——一群酒鬼。再加上,你们也知道,我有一把能够打开巴黎所有房门和柜门的钥匙。三个月来,每天晚上我都亲自去搜查D部长的家,毕竟这关系到我的名誉。而且说实在的,委托人承诺给我的报酬很丰厚,所以我一直不愿放弃。直到我搜遍了D部长家里的每个角落,哪怕是只能藏进一张纸片的角落也不落下。但不得不承认,他比我狡猾得多。”
“那么,还有另一种可能,”我提出,“D部长仍持有这封信,但他没有把信藏在自己的家里。”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杜宾说,“宫廷事务,特别是D部长策划的这场阴谋十分特殊,文件的随时支配权和持有权几乎同样重要,持有者要确保自己随时能够利用这份文件的敏感性来制造事端。”
“利用文件的敏感性制造事端?”我说。
“就是‘搞破坏’的意思。”杜宾说。
“这样的话,”我说,“这信一定还在D部长家里。”
“对,”局长说,“我派人假扮步行强盗袭击过他两次,还仔细搜查过他身边的人。”
“您其实没必要做这些,”杜宾说,“我想,D部长并不傻,他肯定提前想到了自己会被袭击。”
“并不傻吗?”局长说,“他可是一位诗人,我觉得诗人都挺傻的。”
杜宾叼着烟斗深吸了一口,思考了一会儿说:“好吧,也许你是对的。说来惭愧,我有时也会写几首打油诗。”
“能讲讲搜查的细节吗?”我说。
“嗯,我们花时间搜查了那栋建筑的每个角落,这是我的长项。我们在夜里一间一间地搜查那栋建筑里的房间,每间都要花上我们整整一星期的时间。我们先是检查了家具,打开每一个可能藏了东西的抽屉——你们知道的,对于一名合格的警察来说,根本不存在‘暗格’这种东西,只有傻瓜才会在搜查时遗漏了某个抽屉。但我们要找的东西实在太好藏了,不只是抽屉,任何一个柜子里都有巨大的空间可以藏进一封信,所以我们的搜查标准很严格,连一根线头也不会放过。除了抽屉、柜子,我们还检查了椅子,还用长针检查了垫子,又把桌面卸下来,检查了桌子。”
“为什么要卸桌面?”
“有时候藏东西的人会把家具拆开,比如,他们会卸下桌面,挖空桌腿,把东西藏进去,再把桌面重新装上。他们有时还会把东西藏进床头柱里。”
“那为什么不靠听声音来判断家具有没有被挖空?”我问。
“如果把洞里塞满棉花就听不出来了。而且,在这次的搜查中,我们不能发出一点儿动静。”
“可是用您讲的这种方法,许多家具都可以藏进东西,你们总不能把所有的家具都大卸八块吧。一封信可以被卷成一根针的大小,然后,比方说,被嵌入椅子的横档里。你们并没有把所有的椅子都拆开检查吧?”
“不需要,我们有一种更方便的办法。我们用很先进的放大镜检查了每把椅子的横档,还有每件家具的所有接缝处。只要看到一点点近期留下的痕迹,我们就会立刻对它进行全面检查。在放大镜下,一粒螺丝屑也会像一颗苹果一样明显。在家具的黏合处和连接处,任何值得怀疑的痕迹都逃不过放大镜的检查。”
“我猜你们还检查了镜子、橱柜、床和床上用品,还有窗帘和地毯。”
“那当然。这样仔细检查了全部的家具后,我们还检查了房子的墙体。我们把墙体分区、标号,保证没有遗漏,然后像前面一样,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了每一寸地方,包括两边相邻的房子。”
“还检查了两边相邻的房子!”我惊讶极了,“那一定十分麻烦。”
“是很麻烦,但报酬实在是太丰厚了。”
“你们也检查了地板吧?”
“地板是砖铺的,倒还省点儿事。但是我们检查了砖缝里的苔,都没有发现异样。”
“你们肯定也翻找了D部长所有的纸质文件,还有他书房里的书吧?”
“当然,我们打开了每一个包裹。有些警察在检查书本时只是抖一抖,但我们觉得这还不够,所以一页页地翻看。我们还用最精密的测量工具测量了每本书封面的厚度,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了封皮的表面,不放过任何一点儿人为留下的痕迹。有那么五六本书似乎是刚刚装订不久,我们就用长针横着插进封皮检查。”
“你们检查了地毯下面吧?”
“那还用说,我们把每块地毯都移开,用放大镜检查了被盖住部分的地板。”
“墙纸呢?”
“检查了。”
“还有地下室?”
“也检查了。”
“那么,”我说,“你们可能判断失误了,那封信也许并不在那栋房子里。”
“恐怕是这样,”局长说,“那么,杜宾先生,您的建议是什么?”
“全面搜查那座房子。”
“没必要,”局长回答,“我以性命担保,那封信不在那里。”
“我没有更好的建议了,”杜宾说,“您应该能准确地描述出那封信的外观吧?”
“哦,没问题。”局长拿出他的备忘录,大声朗诵了一分钟,描述了那封遗失的信,特别是信封的外观。读完后他就离开了,沮丧得判若两人。
一个月之后,局长又来拜访了我们,我们也和上次一样正忙着。他拿了一支烟斗和一把椅子,和我们东聊西扯。终于,我忍不住问:
“那个,G先生,那封失窃的信找到了吗?我想您最终还是不敌D部长吧?”
“我不如他?好吧,我们进行了第二次检查,像杜宾先生建议的那样。但是,完全是浪费时间,我早就说过了。”
“你之前说,事成后的报酬有多少?”杜宾问。
“怎么了?很多,很丰厚。我不想说明具体的数字,但是这么说吧,如果有人能把那封信给我找出来,我愿意分给他五万法郎。事实上,这件事情拖得越久,性质就越严重。报酬最近也才翻了一番,但是,就算再翻一番,我能做的也不会比现在更多了。”
“怎么,嗯——”杜宾在抽海泡石烟斗的间隙懒洋洋地说,“我真的——觉得,G先生啊,在这件事情上——您还没有竭尽全力。我觉得,您还能——再做点儿什么,嗯?”
“做什么?怎么做?”
“为什么——呼——您不——呼——请个顾问呢,嗯?呼——呼——您还记得阿伯内西的故事吗?”
“不记得,让阿伯内西见鬼去吧!”
“当然,阿伯内西早就见鬼去了。不过,在那之前,有一个很有钱的守财奴,想要找阿伯内西询问治病之道,于是约他在私人办公室交谈。这位守财奴虚构了一个人,以此来向阿伯内西医生讲述自己的病情。
”‘他的症状,’守财奴说,‘有这个和那个。那么,医生,您能给他些建议吗?'
“’建议?‘阿伯内西说,’当然,我建议他去看医生。‘”
“可是,”局长有点儿不安地说,“我很愿意请一位顾问,如果他能帮我解决这个麻烦,我可以支付他五万法郎作为酬金。”
“既然如此,”杜宾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本支票簿,“请给我签一张您刚刚承诺的金额的支票,签完我就把信给您。”
我惊呆了。局长完全被吓傻了,不声不响地呆坐了几分钟,大张着嘴,又惊又疑地瞪着我的朋友,快把眼球瞪出来了。他努力地使自己镇静下来,抓起一支笔,茫然地盯着支票簿,呆滞了一会儿,然后签了一张五万法郎的支票,隔着桌子递给杜宾。后者仔细检查了支票,把它装进钱包,然后用钥匙打开一个写字台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封信,递给局长。这位高级官员带着难以掩饰的狂喜一把抓过信,用颤抖的手打开信封,取出信纸,迅速瞥了一眼内容后,跌跌撞撞地飞奔出门。从杜宾让他签支票开始,他就没有再说一个字,最后又如此匆忙地不辞而别,可真不是他的风格,这太唐突了。
他离开之后,我的朋友开始解释。
“巴黎的警察,”他说,“把他们的那一套用得非常好。他们执着、机敏、狡猾,而且精通警察工作的一切。所以,当G先生详细地讲述他们搜查D部长住所的方法时,我就完全相信,他们已经尽力而为,做了调查所需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