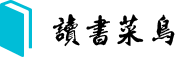《蜕》,[马来西亚]贺淑芳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
内容简介:
那刻有个新的你出生,
也有一个旧的你死去。
——你有想过,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应该遇见
却仍未遇见的人吗?
——贺淑芳
1969年5月13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改变了租住在沙丁鱼楼的桂英一家,还有她朋友和邻居们的生活。
出生于1970年的马来西亚华人女作家贺淑芳,以长篇小说的形式,介入发生在她出生前一年的历史事件。书写事件发生当日,及其后的延宕岁月中,女主人公们的生活。
从1960年代末,到2010年代,她们经历黑暗的记忆,南上北下,接受聚散浮萍的命运,坚韧求生。仿佛被迫陷于永不停歇的流浪,在胶林矿湖,和城市景貌中,逐渐衰老、出生、转变。跨越孤立的境地和破碎的生活,缓慢自愈。
作者简介:
贺淑芳是马来西亚作家,197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州。曾获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九歌年度小说奖。著有短篇小说集《时间边境》(2012)、《湖面如镜》(2014)以及长篇小说《蜕》(2023)。其中《湖面如镜》已经译成英语与日语,在伦敦、旧金山与东京出版。
政大中文所硕士、南洋理工大学博士毕业。曾任工程师、《南洋商报》副刊专题记者、马来西亚金宝拉曼大学中文系讲师。撰写七年后付梓出版的长篇小说《蜕》期间,她曾于2020年夏天,移居台北,在台北艺术大学担任专任助理教授。在淡水居住三年后,于2023年再度返回马来西亚。
目录:
推荐序 近距离与远眺(张亦绚) v
推荐序 小说的在场(童伟格) xi
楔子 1
一 虱子 9
二 青蛇 65
三 蝴蝶 137
四 螃蟹 189
五 蜘蛛 233
编辑推荐:
小说发生在一片星链般的赤道岛屿与城镇之间,
关于女人们所走过的五十年。
——她们是父母离异的女儿(“我不可能看好我父母的婚姻了。”)
——想要友谊却被排挤的少女(“她曾经忘我地跟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当她被其他孩子排斥时,心头就扎入了刺。”)
——初入社会却遭受歧视年轻女人(“她知道他们只是在选择弱者,他们嫌弃她长出来的情感。她很清楚这种嫌弃感如何驱使他人结合起来成为共谋者。”)
——付出爱却只收获背叛的女人(“这个世界上的女人并不是为了当情人、老婆或当小妾而存在的,也不是为了当陪衬。”)
——失去孩子陷入巨大悲恸的母亲(“孩子好瘦,好苍白,好像没吃饭,他说妈妈妈妈不要担心,我会回魂转世。”)
——经历黑暗记忆,却坚韧活到九十岁高龄的外婆(“你愿意记得他,比较起来,这世上还有更多事,很苦涩,让人没有勇气说,下一世出生要全部记得。”)
然而,幽暗的生命中,
也总有记忆微光。
精彩书评:
《蜕》令人感觉是巨大转折。以往只是内容的野性不羁,这下在语言上也放开了。活得不得了。有时甚至感觉到人物就在面前呵气,非常血肉之躯。强烈的生命气息——使用这种热烫风格处理“历史”,颇有艺高人胆大的味道。
——张亦绚(巴黎第三大学电影及视听研究所硕士)
关于历史书写,这正是《蜕》里,最独特的实践:面对真相空阙的冷硬现状,一位必然迟到的虚构文学创作者,不放弃去干预,必然,还会更愈迟到的,所谓“历史自身”。也许,可以更简单说:无论历程如何艰难,《蜕》的落实,就是果敢的宣告——我们不再等待,有人来允许我们,成就死荫之谷里,记忆的破土,生机的赎还。
——童伟格(联合报文学奖得主 台湾小说家)
在线试读:
宋红欢与宋万波
他去了理发店,享受那双手在他头上按摩,那块围拢脖颈,直盖到膝盖的大白布,洗发后,凉凉剪刀沿着朵。走出门,焕然一新。
大都会理发店,那女人叫宋红欢,跟他同姓。红欢本名宋妹仔,十四岁就当学徒,手势纯熟。给他剪发,边剪边问。你也在峇都律做工吗?
是啊。他说跟承包商做,装电线装电话线,修换烂螺丝烂电线,爬高爬低,一脚踢。
听她说闭眼就闭眼,个性真腼腆,怕剪落的发掉进眼里。
“我跟你洗头,洗旧尘,接新年啊。”
宋说他以前只在骑楼下给人剪头发,剪一次一元。
你是哪里人?
宋卡,暹地南部那边。你呢?你又是哪里人?
她说,算是本地人吧,文良港。名字有港,却不是港。
我以前出生的地方,泰国南部的宋卡就是港。
新年怎么不回家?
我没有买到票,今年的票很难买,太迟买。
他笑声很低,跟别人不一样,不像那些大声公,趁过年,就成群结伙到处开台,但他样子也很体面,脸有点方,面目端正,皮肤晒得很黑,跟马来人一样。个子不是太高,说话不多,跟人吵架不能赢。他凑不进那圈子,就退出来,看来满老实的。不过事实如何,也很难说,毕竟她还不认识他。
他说他父亲以前也是帮人剪头发的,到处去剪。后来吸鸦片,做仙,如果不穿衣你会看到他胸整排骨可以打吉他。要是起得了身,他就会想去咖啡店后面赌博。
里面有个有轮子的白板,可以拉来拉去,用来遮赌桌。赌起来三天三夜不回家。我也忘记哪一年,阴天,傍晚,我阿爸被赌场踢出来,听到有人说要打他,就跑去躲在车站旁边的工地里。大人叫我去喊他,我去叫,爸爸,爸爸,他却不认得我。第二天,就没有了,下大雨,他溺死在工地,刚做好,那沟渠不能通水。
啊,她吃了一惊。他那时才十三岁,以后就自己吃头路。
她本来不觉得自己跟他同姓,宋是养父的姓,但真正养大她的人是养母洪亚喜。养父有第二头家,生了六七个孩子,就无暇顾及这头家了。打从一开始就不太理她,连给她取名都懒,跟注册官报名时就说她叫“妹仔”。出来工作后,她给自己取名红欢。她跟店里的人说,不要叫我密斯宋,叫我红欢,我无姓。
养母这生并不好过。大概是在被英军驱赶,随着整村人颠沛流离的那些年里,这对夫妇在无意中收下了她。可是养父毕竟不喜欢她,照料她的始终只有养母。她真不明白何以一定要让她跟那人的姓?如果可以改姓,她一定要改成洪,跟养母。
她常不明白这世界,到底是什么道理在给人排序?有的人注定被爱,有些人明明拥有许多东西,却老提防像她们母女俩这样什么都没有的人。
一颗橙切成六份,摆在桌上,别人很快就伸手拿走。其他兄弟姐妹争着跟父亲说看见什么、听见了什么、吃了什么种种,她也想找机会插嘴说,努力了几年,想告诉父亲自己也遇见什么、学会什么,一次次,养父脸冷得跟冻鸡屁股一样。其实也没什么,不是不能受,起初她不知自己是养女,知道后,懂了,就省回力气。倘若以养父平时凡事以利益和成功定论的观点来看,她不过是不重要的妻子养的无血缘孩子又是女的,故此,更是三倍地无相干。那以后就彼此彼此吧,她也可以切割关系,没什么大不了。
某天宋万波来,跟她说了个笑话。
他讲一个人,某个先生非常斯文,喜欢把东西弄得很整齐,还喜欢把一切都调整得规规矩矩。他瞧不得一点,规定佣人要每天把家里抹到一尘不染。不过有那么一天,他脱下鞋子,脚臭,嗅。一嗅上瘾,以后他就开始嗅自己身上每个地方的气味,嗅异味。
她听了噗嗤笑出来,宋万波似乎也很开心。大雨敲屋檐吵聋,他们得大声说话。他好像不太想走。当然因为这是雨天,雨大得天桥上的招牌字都蒙了,马路上都是水,从天空湿到地上。
你喜欢吗?剪头发,洗头,挖朵。他问。
不做这个还能做什么,十几岁学到现在,她说,我都不会做别的。
天色越来越暗,才三点钟,阿娇姐冒大雨,从银行赶回来,都要淹水了,阿娇姐大声说,一边收雨伞,肩膀衫袖湿透,没客的了,开灯也是浪费钱。说着就把唯一一盏亮着的柜台灯都关掉,整间店灰暗下来。又说,阿生你今天不用做工呀,我们不做生意了,老板娘说不要浪费水电,叫我们关店,万一吧生河淹水了,我们搭不到车回家。
她看着他在大雨里跑过马路,像只牛跑起来那样过,竟没用行人天桥。
孤男寡女你不怕吗?阿娇姐问。
新村地很平,没有需要爬坡的,只有去割胶时走山路才需要。一路上有电灯杆,一支支,很多年都是空的,没有接上电线,好像只是给州政府插了伫立那里,不知为何遗忘了,有那么一个角落,被世界遗忘。她记得有一次割胶,快天亮时,割胶割到胶林边缘,靠近马来甘榜,突然听见奇怪的动物叫声,走近去,看到羊,是马来人养的羊。羊的眼睛从木板栅栏板缝里盯着她看。
看到那羊栏,就觉得自己已经出了平日的范围,到了另一区丛芭,像是世界的另一边。新村养鸡养猪,就是没有人养羊跟牛。
她就好奇地看着羊,羊的眼睛很大。她没想到羊是食物,因为小时候养母带她去,观音说她不可吃牛羊。想到羊原来可以吃时,那只羊突然朝她咩,很响,好像很愤怒,一直叫一直叫。
九岁那年,她们家搬回新村,一路睡睡醒醒,睡前还在一处,醒来后已经在另一处了。好像有梦跟现实融合在一起,决定你人生要处在这还是那。
新村都有寺庙,观音济公大伯爷。我们烧香,到底是在求慈眉蔼目的观音让那梦快点醒,还是求祂不要揭穿,让我们继续做着舒适好梦?
天公诞之后连续几天雨。过桥时往河面望,河水像一条朱古力色大蛇在翻滚,听闻有些地方已经淹水。
宋有六根手指,多出的一根从拇指底长出来,很短小,好像没有什么力。
一个在附近工作,常来店里的女招待莲花与她男人小刘,一个德士佬,逐渐混熟。四人一同聚在理发铺后院,吃榴莲。宋抓巴冷刀,那根多长出来的拇指,轻轻搭在刀柄上。持刀一劈到底,好像还满轻松的。
我真是好欣赏你这把刀,莲花问,哪里找来?
偷来的,厂里面的,宋说,只是顺手拿来用。
刀用好几张报纸包着,然后装在一个纸袋里。他就提着那纸袋,沿着人行道与骑楼下方走过来。虽然不是很远,走路大概只十分钟,但也可能会给警察叫住检查,总之没碰到算是好运。
三月里,傍晚七点多,宋万波独自穿过巷子,被烂铲莫名其妙殴打。警察来到,把所有人不由分说都捉上车,到了警局,他忍着痛直到写完口供签名,才送去医院。
起初她不知这件事。知道时,他都快出院了。听刘说,对方总共有三个人,他们跟他到巷子,就忽然凶神恶煞,拳打脚踢,他从后巷穿过茶室一直逃,逃向大马路,向十字路口人多的地方跑去,不然玻璃樽什么都用上,就没命了。
宋那天没有把刀带在身上的,因为切过榴莲后,他就把刀留在理发院,不知怎地忘了带走。
也许是刀引来的杀气。这把刀不懂以前是谁用的呢?一直留在铁厂里。真有些诡异。也许是刀找人。有些物件就是会有那种能量,阴森杀气。说真的,宋说,那天我怕的时候,怕死,还真的有个冲动,要拿刀斩人。可是一摸,原来没有刀,就在心里一冷,觉得无望时,忽然好像眼睛反而变清楚,突然看出旁边有出路,就跑出去。
年初五,她跟莲花出门,宋和刘也一起。孩子找不到鞋。鞋子哪里去了?“刚才脱放第三格的,”孩子说,“不知给踢到哪去了。”新买的鞋子,有点心痛。“都叫你要放进房间。”“才一下子,”孩子抗议,“哪里知道突然来那么多人。”他们租房的楼下,二楼有个老人家,刚从医院载回来,隔着木板墙,听得见男人女人大声问,阿爸你还想见谁?你要找谁?三哥三嫂在路上了。有人小声说,他从昨天就看见叔公叔婆来叫他,时间到了。里面没有阿公?我都没看过阿公,人死落地生根。殡仪馆,哪里才好又便宜。给阿爸穿什么衣服呢?好鞋都没一双。声音陆陆续续从板房传出来,听得见啜泣声。她和九岁孩子继续在阶梯上,一层层找,看了又看。男孩的脸颊很红,满脸头发脖子都是汗。那是一双棕褐色的塑胶皮鞋,里面有小熊图案,鞋侧边还得扣鞋带。一排排阶梯都是鞋,奇怪他的小鞋子就是不见了。宋本来远远地在路边等,看看就走来,蹲下帮她找。
鞋是怎样的?给穿走了,孩子快哭出来。有熊仔。是黑色缚带那双吗?我自己找可以。她说,心里烦躁。她想放弃了。孩子蹲在的梯级那格,往上望,往下望,极力远望,四处都是别人的鞋。泪珠往下滑,落到草尖上一点晶亮。泪大颗大颗地冒出,草尖上那点晶莹泪珠模糊了,蒙了,他用手背抹泪,草尖上明明灭灭,原来是一只萤火虫。他看着那昆虫,趴在草叶上,衰弱模样,没力了,翻个身,四脚朝天,无法抓着任何东西,但腹尾那点光还在闪,大白天的星星。孩子一直看着直到那光不再亮为止,萤火虫死了就成为一只普通的虫,手指一碰,虫掉到泥土里,被草叶遮住。孩子满脸的泪痕汗痕彻底干了,现在他是一张猫公脸。找不到,死心了。
他只好穿旧拖鞋出门,不见了就是不见了。他失去了一双鞋子,被穿走了。母亲说不会买新的,你以为我很有钱。你妈骗你的,其中一个男人说。他们一伙人去大排档吃面,茨厂街的云吞面与咖喱鸡面,士思街的叉烧面跟冬菇鸡翼面,填饱肚子。不找可能又会出现,另一个女的说。
孩子给她读了一则奇怪的故事,后来回想,就像预兆一样。“发生了大件事……一个黑衣的人,巡过了整条街。”刚上二年级的小孩,读出的声音,像水一样凉爬上脖子,好像有积雨从屋檐漏下来,一阵寒意。也许只是昨晚睡不好,早上又没什么客人。
她问他,你刚讲什么?孩子说,不是我讲的,是这里写的,一个小故事,就说城镇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大家都关上门,不敢出声。只知道,来了个穿黑衣的人,巡过整条街,不久市场就变得萧条,可是没有人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些天,理发店没什么顾客。选举刚过,反对党大胜,街上游行亢奋了整整三天,顾客就不进来了。五月十二号理发店照常开工,但提早关门。五月十三号,阿娇姐说要早关店,因为下午有另一班人示威,人家说会是巫统的人,有人说会烧屋,有人说这无影的,谣言。阿娇姐说宁可信其有,午后四点,阿娇姐跟她一起拉下铁门。
从那天开始,一直到戒严结束,她都没再见到宋万波。
再见到宋万波,是九个月以后的事了。
他背后挨了鞭笞,痛得发抖。泰式酸辣面之类都不能吃了。呛咳得厉害。咳到严重时会漏尿。他不说,太丢人了。她装着看不到床单上的尿迹,只说,是不是太勉强了。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跟我说,痛的话跟我说。她说。
不过他不会说。其实若换成是她,也可能不会说。
见到宋万波那日,云层很厚,是个阴天。她提着许多东西,走在骑楼下方,大老远就看到他,他也走在骑楼下方,而且面朝她,可是,他却没有看见她,似乎在想什么,头发没有洗,好像几天没洗澡,嘴唇动一动的,像是在自言自语。
即使那么远,她也看得出来,他不一样了。
他似乎想过马路,可是刚好来了一辆大啰哩,他又退后一步,视线跟着那辆驶过去的啰哩,头转过来,表情忿然,她不忍心了,心想,他可能看到她了,只是假装没看见。她就举起一只手,朝他大力挥摆。
她奔过去,提着一大袋米粉、罐头。靠近了,才看见他脸上那划长长的疤痕。
你好了?回来开工了?
差不多,他说。
差不多什么,她不明白。她不敢看那可怕的疤痕,就望进他眼睛。你要去哪里?
他没有回答她。他不知道要去哪里。
他搓搓自己的眉眼之间,以一种怪异的方式搓自己的脸。他的手指,上次殴打过后扭伤发肿的食指与尾指,造成的扭曲看来像是永久的,再也不会恢复了。当他把紧握着的右手掌摊开来,她明白了,他以后再也不能好好装电线、敲钉子或做细功夫了。
去我那里坐一下吧,她说,陪我走一下。
他一拐一拐地走在她旁边,双肩一起一伏。她看着他投落地面斜斜的影子,也是这样一起一伏的。她叫他来,只因为她想不到别的理由。很多我们以为可以安慰的话,不要想太多、留在家里耐心等,全都是废话。他当然会一直在心里烦这烦那的,再回去建筑地盘做水泥工也做不来了。得去找人,得再去拜托人。
他们慢慢走过杂货铺,一个员工扛着一篮蒜头,从通向人行道的阶梯砰砰踩上来,啪的一声放落店门口。经过一间土产店,有个男人正昂头上望,伸长手臂,把什么一包包的东西挂吊上方的钩子。在炒咖啡豆的店里,一个年轻女人正持铲搅一口黑黑大锅,像下雨沙沙响。一间中药店。一间堆满砂煲罂罉。转弯处有个马来修鞋匠,蹲坐小凳子,用支小槌子咯咯敲掉一双皮鞋的后鞋跟。
她觉得他们两人像刚复活回来还不适应身体的小木偶人,小心翼翼地踩下楼梯,越过小巷,又踩上另一边的三级小楼梯,走上另一排店屋骑楼。终于走到理发店前。
推开那两扇小门扉,今天店里只有一个中年女顾客,阿娇姐正给她剪头发。一边剪,一边转头望他,跟他打招呼,哎,阿宋,坐一下。店里的年轻女学徒把报纸拿给他,不晓得他要不要抽烟,还是给他递一支。他叼着了,手不顺,还是能夹着烟。点着烟时,就把报纸搁放一旁。
她的孩子一直站在厨房门边,孩子却没有靠近他。那具身体令孩子感到陌生,还有他脸上的疤痕。一会儿,孩子又稍稍移前一点,走到柜台旁,脸侧靠柜桌,以好奇、陌生、考虑着什么的目光望着他。
才不过关了八个月,他变得很瘦弱,脸的轮廓突显,多了一条疤痕,可是整个人已经像给撤换掉了。身体坐得弯弯的,仿佛从前的他从胸部凹陷落去,换了另一个陌生人从内里露脸出来。
来了一个顾客,她就去给对方理发。才剪到一半,听见有人推开门。再转头看,宋万波已经不在店里了。
一整天给人剪发,不知为什么一直弄跌东西,成天都得跟顾客道歉。不是弄跌人家放在柜台的钥匙钱包,就是弄跌本来插在腰包上的梳子、指甲剪。握着剪刀,给顾客修刘海,剪上鬓发,忽然手就颤抖起来,手冷冷的。
这种害怕,这些年来不曾停止过。去年年底,英镑贬值,连累旧钱币也跟着贬值。她很迟才知道,立刻挖出铁罐里衣柜的钱钞钱币,连同印有英女皇的钱币,大概百来块,立刻拿去杂货店买牛油罐头白米。那几天,巴刹里,有人搥心肝跺脚大哭,因为她知道得太迟。有个女人才四十几岁,大家就讲她是个“绝望的老姨”,丈夫早早死了,有六个孩子,存的储蓄全都是英女皇旧币。
三十岁就被唤阿婶,五十岁就老姨。她觉得很不甘心,女人生命好像早早就给强硬地截断,当成养孩子做保姆做女佣。中秋节茨厂街又有火烛光顾。不知怎地,一连三年同处失火。木屋最易着火。跑出来的人只剩身上一套衣裤,什么都没拿,很多女人把钱存在罐子或扑满里,一无所有。
一直到七月,各种零星冲突,殴打,火烧屋,都没有停过。峇都路、怡保路,好靠近的地方,一直都有人在放火烧屋,烧住屋,烧店铺,烧仓库,烧工厂。
她租住殖民旧屋楼上,几乎每间房都很多人。她跟四个女人一起合租一间大房,再加上各自的孩子,总共有七个人同睡。每天上工,尽可能把孩子带着,楼上楼下共有十七八个人,共用一个厨房、两间浴室。留在宿舍,孩子好易被人虾。把孩子带在身边,做上整天,回到家就累死了,洗澡后才跟孩子说说几句,很快就睡着。
偶尔也有难睡的日子。天气热。夜里屋内街上,什么动静都听得分明。听得外边狗仔长吠,远处也有另一声狗吠呼应。不晓得真是有幽魂骚动,抑或流浪狗仔也寂寞凄凉。连街灯下有飞蛾昆虫扑火声音都听得清楚。每次有人走动,屋子就像水上船一样,浮吓浮吓。
戒严过后的一个月,警察到处扫荡妓寮、按摩院、赌窟。整个吉隆坡的中南区,尤其是惹兰拉查劳、怡保律、峇都律一直到何清园,天天都有警车咿呜咿呜进出。
五月底,莲花上班的夜总会,才刚开工,很快又被检查了,她说天天吃西北风,等拾苙。
金巴黎,警察好像只是作势冲进去,不用拼搏也不用开火,顺顺利利押一堆人出来,关进警队囚车。很多人远远地从对面骑楼下看热闹,大家说他们捉的都是小鱼仔和未成年少女,重要的台柱与大佬早就避开了,全都是做个样子交差罢了。
报上说有五千个被抓,这数字里面,宋万波被逼当了一个。鞭笞过后,他说每逢雨天他就关节痛。有时候严重起来,握不住碗杯,就从手中滑脱。
天还没亮,她就下楼洗脸。孩子要去循人中学上课。车来了,学生排队上车,异常乖静。她去买早餐,走过成记酒楼对面,突然看见宋万波在过行人天桥。她不禁大老远叫了一声,车水马龙,他没听见。她跟着追上去,楼梯两边都有乞丐,不是麻风残缺,就是年纪看来老大。也有女人带着孩子行乞。近日,每座天桥都是这般景象。
看着宋万波背影在楼梯上方,看似辛苦地上楼梯。她心里忽地没了勇气,几乎想转身回家。可是宋万波不知怎地,好像感觉背后有人一样,一转头,就看到她。
他的眼神似乎很惊讶。他脸颊上那道从左眼角斜划至鼻翼的长长疤痕,已经褪色了,不那么触目惊心。她从下方看着他,奇异地觉得,那种过往看到他,莫名眷恋的感觉又回来了,便走上去,问他,你做什么?近来好吗?
我哪还能做什么?我要来这里打地铺。
她有点不知怎么回答。
开玩笑的,他说。
他们来到天桥中间了,很高,即使不挨近桥边往下望,也能感到天桥高得让人畏惧。铁栏杆之间透风,两旁的乞丐,就靠着那铁条坐。那空隙还好,不至于让一个小孩钻过去,但一只猫是可以的。她极力远眺,别往下看,就能把这里想象成平地。桥上的乞丐都不怎么害怕,可能麻木了。当中有个印度人,恤衫卷起,露出大肚子,对天躺卧,呼呼大睡,似乎不在乎自己什么也没有。
她常看到这种景象,车站、骑楼下,无论看多少次,都觉得无法坦然,然而又不得不硬着心,仿佛无动于衷似的过去,因为实在帮不了。她觉得自己算是幸运的。到头来,免于流落街头的命运,总是幸运。
后来他们慢慢下了天桥,宋万波才告诉她,他小时候也没有地方住的,只是跟阿爸一起。
他到哪,我就跟到哪。
他们睡三轮车,巴士车,有时候去他阿爷睡的鸦片棚。马路边,天桥,打地铺。
她不太想跟他分手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