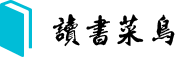《夜行者:从荆轲到铸剑》,何大草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4年出版。
内容简介:
何大草历史小说集,收录代表作四篇——
《一日长于百年》《鲁迅先生安魂曲》《李将军》《衣冠似雪》
在死中活、在活中死的卞先生;弥留之际在记忆的街巷游走的鲁迅先生;孤身追逐命中之虎深入胡地的李广;用优雅的双掌握住嬴政刺来之剑的荆轲……四段历史,四场梦,四面镜子,生与死的映射,其中是你我。
在这部集子里,本真的生命经验将过去的时间桥接进未来,连贯为一条具体可感的河流,而测量水位的总是人性。就此而言,这本书提供了从历史之水底观察现实之水面的潜望镜。
作者简介:
1962年生于成都少城,1979—1983年就读于四川大学历史系。
代表作有长篇历史小说《春山:王维的盛唐与寂灭》《金桃:吴道子,他的世代与风尚》《崇祯皇帝·盲春秋:明朝末代皇帝的生与隐》,以及《隐武者》《拳》等。
以写作、讲授写作为业,兼事绘画。
樱园何大草写作工坊指导老师。
目录:
一日长于百年
鲁迅先生安魂曲
李将军
衣冠似雪
四则记忆(代跋)
编辑推荐:
有生,有死,有爱,有憎,也有怕
《春山》《拳》《隐武者》作者何大草中篇历史小说代表作★洞穿时间的表象,切入生命的内里
“面对复杂的生命个体时,是乏力的。总是要给出结论的,然而,我找不到结论。理性不能言说的地方,叙事是最好的选择。我想用小说,重现鲜活的生命。即便是生命的最后一夜。”
“风没有了,雾将散未散,路越走越宽,灯光也愈是亮堂……”
在线试读:
四则记忆
(代跋)
一
卞先生的原型,源自一本旧书,名为《我认识的××》。当时我在念中学,却正值书荒年代,就到处去借书、访书。进了邻居、同学的家门,但凡看见一本书,抓起来就读,无论好坏,囫囵吞枣了再说。消化、反刍,或者回味,可能要等很久,甚至十年、二十年,还不止。
记忆中,《我认识的××》,封面是灰白的,没图案,仅有一行书名。而且没印出版社,属非正式出版物。但,不是私人盗印,更不是手抄本。这类书,当时出了一些,似乎有个统一称呼,叫作“内部读物”。机关单位、机关干部家,多少会有一两本。
我已记不得是从哪儿弄到这本书的。读了之后,觉得很神秘、很好奇,却又很不过瘾。之后,我一直留意××。只要是有关他的记载,都有兴趣读一读。不过,能找到的,并不多。
我于是在脑子里构想××的故事,他的容貌举止,他的诡异遁去,以及他对生的迷恋。渐渐地,卞先生浮现了出来。但卞先生和××已经不是同一个人。说卞先生的原型是××,也不够准确。或许,正确的表述,应该是:××乃触发我写这篇小说的头一个灵感。
写这篇小说时,我到大学任教还不久。
校园在东郊的狮子山上。树林、教学楼、宿舍楼,散落在绵延起伏的坡地上。墙外,是田野、菜畦、柑橘园、桃林,还有成昆铁路。再望远一点,可见横亘两三百里的龙泉山脉。
我的住所,在南墙内一幢很旧的红砖楼上。上课铃声传过来,已然模糊。而墙外农家的说笑声、犬吠声,却清晰可闻。偶尔,一声尖锐的火车鸣笛后,四周都陷入大的寂静。我就是在大的寂静中,写着《一日长于百年》。
写得极慢。写累了,去校园里走一走。很多师生都还不认识,坡地的盘陀道也给人新鲜感、陌生感。陌生感带来了距离,我喜欢距离,觉得松弛、安宁,而且安全。有时候,夜晚我也在校园里盘桓,嗅到桂花的香味,看月亮从树梢升起,觉得活着真是奇迹。
飞来了几只马蜂,在我卧室窗户的左上角筑巢。我觉得可笑,天下之大,怎么会选这么个光滑的角角呢?我倒是没有惊慌,隔了玻璃窗、钢纱窗,马蜂再狠,也伤不到人。
每天,我写一阵小说,就会去看看马蜂。马蜂越来越多,几只变成了一群,巢也有拳头大了。再后来,巢到底筑成了,几乎有篮球大,在窗户角上粘着、悬着,很好看,也很危险,似乎随时会被一阵风吹落。但始终都没有。蜂子在巢里飞进飞出,悠然地,透过玻璃与我对视,像看老熟人。
这篇小说写了几个月。马蜂窝与我比邻而居,相安无事。我观察马蜂,觉得有趣。马蜂也会停在巢边,打量我,似乎觉得我也有趣。日子冗长,时间无限,有时会觉得,活着也真是无聊,无边无际。
第二年五月,《一日长于百年》发表了。七月,我和红砖楼的住户都搬离了。红砖楼被拆毁,夷为平地。马蜂去了哪儿,谁也不晓得。也没有人问过。
二
最初读到的《鲁迅小说选》,也属内部读物。不过,封面多了他的一帧图片,极瘦而严峻、倔强。那时候,我还在念小学,鲁迅的作品,读来有点懵懂。印象深的是《风波》,因为里边写的几件道具,感觉很好耍,譬如,赵七爷穿的宝蓝色竹布长衫,七斤的象牙嘴白铜斗六尺多长的湘妃竹烟管,以及钉了十六个铜钉的饭碗,等等。至于一根辫子跟国运巨变的关系,我不是很有兴趣。
一九九二年四月,我买了一套《鲁迅全集》,把他的所有小说重读了一遍,很是叹服。也读了一些他跟人打笔仗的杂文。不打笔仗,不带火气,写得超然、峭拔而又切实有力的,是《中国小说史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智有趣,我也喜欢。
后来,又读了不少关于鲁迅的回忆和传记。感觉到,他的内心,尤其在晚年,充满了矛盾。他写了许多尖锐的文章,疲惫而又矍铄地挑战和应战,尤其是那篇被认为是绝笔的《死》,他说:“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为自己的内心塑了一面坚硬的壳,壳上写着“恨”。然而,即便是他亲口所说、亲手所写,我也以为这不是真相。
我曾经很想写一篇关于鲁迅的,谈他的生死爱憎。为此,搜集、阅读了相关材料,作了笔记,写了提纲,积攒的素材和气力,足够把这篇写成一篇很长的长文。
但最终,我写成了小说。因为,面对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生命个体时,是乏力的。总是要给出结论的,然而,我找不到结论。
理性不能言说的地方,叙事是最好的选择。我想用小说,让这个入土为安的巨人,重现鲜活的生命。即便是生命的最后一夜。
“‘我把你们一个个都宽恕了。’这是他对世人说出的最后一句话。然而,他们没有听清楚……”我也许写了一篇违背鲁迅本意的小说?
大约二十年前的夏天,我旁听了一个座谈会。主角是当年的高考状元,以及他们的班主任,还有几位教育专家、媒体从业者。班主任在介绍了教学经验后,状元发言。文科状元是个女孩,沉默了片刻,似乎在忍住什么,但终于没忍住,一开口就哭了。她哭道:“我不懂,为什么要让我们读鲁迅?读都读不懂……为什么还要读?”
我吃了一惊。与会者的反应,我已忘记了。我虽吃惊,但也沉默着。我能说什么?直到今天,女状元哭着说出的话,还不时回响在我朵边。
三
我读过的书中,复读次数最多的,是《水浒传》。它的前七十回,我大概读了百遍。
我儿时先看的是《水浒传》连环画,上了瘾,然后找的原著读。连环画中,我最喜欢的是花荣。他在《清风寨》中亮相,少年英气,五官精致、细腻,且箭法如神,跟鲁智深、李逵这一路好汉,大为不同。唯一的遗憾是,他虽有娇妻,却只是个符号。在这点上,他又跟多数好汉很相似,活像禁欲主义者。
花荣绰号小李广。因为这个绰号,我才晓得史上有李广这个人。到可以懵懂读《史记》时,我马上挑了《李将军列传》,磕磕绊绊读了几遍。后来,还熟读了两句唐诗:“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说李广夜醉,看石为虎,一箭射去,竟把箭射入了大石里。
李广自然比花荣更厉害。他不仅是神箭手,且是个好将军。他跟匈奴人打了一辈子仗,匈奴人谈之色变。可见,他的英武和将才,都堪称卓异,显名于长城南北。
可他也比较走霉运,不得志。所以,王勃这八个字才传诵了一千多年,被认可、被叹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何以会如此?谁也说不明白。说是命吧,这自然是对的,可也很有点敷衍,等于没有说。
我也没有答案。只是多读了几本书之后,发现李广这个人,活得很个人。这句话的意思,可以这么来理解,他的活法,最终在于自己的感受。可能起初是克制的、有所把控的,但到了把控不住的时候,也就他妈的豁出去了。他一度解甲归田,因为狩猎晚归,被小小的霸陵尉羞辱。之后他再度披挂为将,就把霸陵尉诱至军中,一刀砍了脑袋。“死灰复燃”的韩安国,“胯下之辱”的韩信,得志后都能够宽容施辱者,相比起来,李广的气量算是小的了。但,这种小,也是李广的真性情。因为这种真性情,他虽不得志,却也活出了一个青史留名的人生。
《李将军》发表后,有朋友读了对我感叹说:“写得还是不错的。不过,比起《衣冠似雪》,咋就多了几分颓气呢?”
写《李将军》时,我三十八岁,写颓气似乎是早了些。不过,颓气的确是有的。但,除了颓气,也还有热气,有暖融融的黑羔皮毯子,还有袍子下炭火般滚烫、鱼一样光滑的身体。这是给一个孤独英雄的慰藉。他和她相互的慰藉。
顺带提一笔,《李将军》中有个先生叫王朔。有人说:“这是在影射某人么?”自然不是的。《史记·李将军列传》中,的确出现了一个预测吉凶祸福的先生,就叫作王朔。在这儿,纯属于写实。
四
一九九四年一月,我开始撰写《衣冠似雪》。这是我的第一篇小说,也是朋友间的一个约定:如果写砸了,就封笔,安心读别人的小说。
写谁呢?我脑子里一下蹦出的名字,就是荆轲。我是历史系的逃兵,但逃了多年,还是藕断丝连。写小说,逃不掉的,还是历史小说。
我晓得荆轲的名字,源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荆轲的形象是个小丑,他企图通过行刺嬴政来阻挡历史的进程,结果自取灭亡。这比螳臂当车还要可耻、可悲、可怜、可笑也(此处借用一个中学同学的作文)。尽管如此,我还是佩服荆轲胆子够大,不怕死;刺杀的场面也惊心动魄。
在历史系念大一时,有位室友去省展览馆看了画展回来,对我说:“有幅画荆轲的,你可能会喜欢,去看看吧。”我于是就去了。展厅里挂满了画,我一一看过去,看到荆轲,果然心头一动。画的不是图穷匕见的一刻,没有抓扯、厮杀,是很静态的画面:易水告别。燕国的贵族跪倒在荆轲的脚下,而荆轲仰头看着秋水长天、两行大雁。他的脸色是苍白的,没什么表情。
这幅画我至今记忆犹新。它从视觉上颠覆了我之前所知的荆轲。后来,我读了《史记·刺客列传》。里边讲了好几个刺客的故事,个个都很动人。但最让我感觉滋味难言的,还是荆轲。
此后好多年,我一直在脑子里营造自己的荆轲。譬如,看了电影《敦煌》中佐藤浩市饰演的赵行德,我就会想,荆轲是否也这么看似敏感、脆弱,却又持有与他人迥异的见识?他是士,通音律,知诗文。不是壮汉、莽汉,也不是受恩即报的屠狗之辈。
《衣冠似雪》动笔时,正值天寒地冻。书桌下放了只四百瓦的红外线烤火炉,脚板暖了,则一身都比较舒服了。我有时候写到半夜;有时候后半夜起来,写到天亮。写不出来时,就抽烟,一支接一支。小书房里烟雾弥漫,呛得人流泪。于是就开了窗户通风、换气。冷风吹进来,凛冽刺骨。只好马上关窗。如此循环往复,弄得心烦,索性把烟戒了。世上的作家,因写作而嗜烟者,比比皆是。因写作戒烟的,估计少之又少,我居然算一个。这也是奇了。
《衣冠似雪》是我唯一用纸笔完成的小说,手稿至今保留着。用钢笔写在报馆的稿签纸上,每页三百格,页脚印了淡绿色的报社名字。我写字不善巧劲,很费力,写完一页,就手骨酸痛。好在写得慢,一天写不了多少字。有一天上午,我从稿纸上抬起头,看见窗外正在飘雪花。雪花不大,但密密的,漫天飞舞。我觉得很欢喜,仿佛雪花是从我小说中生长出来的。
写到春暖了,一稿完成,有五万字。二稿下来,删了几千字。三稿又删了几千字。后来请一位做工程师的老同学帮我录入电脑、打印出来,匀整得就像已经发表了。素衣白袍、超然淡漠的荆轲,就活在这些文字中。他是先秦的最后一个著名刺客。一个失败的刺客。一个可能被误读了的刺客。
一九九八年,我的小说集《衣冠似雪》出版时,秦晋老师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后记。他说:
在《衣冠似雪》中,叙述者并不是站在燕国或者太子丹的立场上,把秦王嬴政仅仅看成是一个简单的暴君,荆轲也不是为报答太子丹知遇之恩而慷慨赴难的壮士,太子丹更不是礼贤下士、宽厚仁爱的志士,他们都比人们已经习惯认同的性格角色复杂得多。
我赞同和感谢秦晋老师的阐释。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总是拙于分析自己的小说。当朋友问到《衣冠似雪》的主旨时,我常借用小说中的一段对话来回答。或者说,避而不答。
“那么你是一定要去杀掉秦王嬴政了?”
[……]
荆轲说:“是的,我这就要去。”
“是为了太子丹吗?”
“噢,不。”
“为谁呢?”
“我曾经想得很清楚。但现在已经忘了。”
《衣冠似雪》之后,我写了《如梦令》,故事为李清照南渡。那是我用电脑完成的第一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