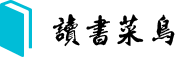《遇见陶渊明:陶渊明心灵游记》,张君民著,大有书局。
在《一蓑烟雨任平生——苏东坡生平游记》两年之后,张君民又推出新著《遇见陶渊明——陶渊明心灵游记》,时代从风云变幻的大宋王朝跳跃至刀光剑影的魏晋之际,风格由酣畅淋漓转为清远淳古,颇得苏公“随物赋形”之妙。
何以有此变化?按照作者自云:东坡先生已是真性勃发、“千古风流人物”,何以尚拜渊明为不可企及的文章高峰、节操典范?——所谓“渊明吾所师”“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带着这种疑问,作者将目光再度前移六百多年,聚焦在这位浑身静穆而又面目飘渺的“田园诗人”身上。其主线便是追溯剖析传主之人格节操之形成,“遇见”陶渊明的时代、家世、文化浸染、生平实历、诗文作品,以期还原真貌、洞悉心灵。
时代、人格与文格的交融互织
《遇见陶渊明》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时代勾勒清晰明快,简明扼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动荡黑暗的时代,要能捋清其间的政治纷争、权力更迭、历史消长,非下一番大功夫不可。而作者却能游刃有余、娓娓道来,不见局促窘迫之感。陶渊明处于晋宋之际,而著者却从东汉和帝切入,长辔远驭,追根溯源。
第一章“时代”的总题为“八表同昏平路伊阻”,虽借用陶氏《停云》诗句,亦可见识见。这一章下,“丛林法则”“魏晋风度”“无奈的反弹”这三节标题继而揭示了时代真相:“知识与仕宦的世袭,是形成士族门阀的主要原因”,“累世相传历数百年而不坠的经学之家就成了所谓的‘门第’”;“苦难孕育辉煌的艺术”,“酝酿出另外一种生命力量”。这种历史的叙述其实贯穿始终,不仅仅限于开篇,使得人物的活动始终有背景可查,“随叫随到”,显示出著者对历史的熟稔。
其次,陶渊明的诗文成为研究的重心。不仅对其家族的梳理从《命子》一诗开始,而且陶渊明本人的生平经历、所思所感亦大都通过诗文为证,所以该书从框架上可称人物传记,但却以诗文作品为核心分析内容。这不仅仅由于传主的生平经历比较简单(陶渊明一生游宦虽前后十几年,但时仕时隐,断断续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乡村度过,琴书自娱、躬耕劳作,缺乏如苏东坡般惊涛骇浪的宦途生涯),而且诚如宋立民先生在评前作《一蓑烟雨任平生——苏东坡生平游记》时所说:“就‘纪实性’与‘即时性’而言,诗词在传记中的‘史料价值’,是不下于书信与日记的,而且其间的情感更为丰富而直接。”故而本书称“心灵游记”,是突破了一般传记著作的写法的,使读者直面传主的情感心理,由此辐射开去,与诗文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共同构织成一个广阔的精神世界,由点及面。
《遇见陶渊明——陶渊明心灵游记》张君民中央党校出版社如在“先贤”一章中,即让读者逐一了解陶渊明笔下赞美和崇尚的古圣先贤,由此去挖掘陶渊明的精神来源。而在“归隐”一章之“南村素心人”一节,则从陶渊明“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诗句寻索开去,将颜延之、慧远法师、周续之、王弘、殷景仁、张野、羊松龄、庞遵等交游对象纳入叙述行列,既展示了传主的平生事迹,更扩充了历史与文化的空间。
当然,更重要的是全书对陶渊明精神世界的合理而优美的发掘论述。从“那可是当时开得最卑微、最朴素的一朵文艺小花”,到“他的文学世界成为其后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归宿”,其人格质素何以形成?作者认为,陶渊明一方面“有着曾祖父陶侃出身寒微所具有的质朴和勤奋”,另一方面“也有着外祖父孟嘉士族阶层所具有的高贵与镇静”,陶渊明追溯与寻找着的是一种荣耀、一种高贵,甚至是一种不屈、一种规律和选择。家世背景成为陶渊明性格人品的重要基因。
放眼陶渊明短暂而又漫长的五十六年人生,作者指出那是“一条人格与文格交融互织的人生脉络”,是“一条以儒家的仁厚、孤介为主线,伴以道法自然的率真与知足,形成他独有的穷困潦倒却又自足尊严的奇妙人生之路”。从质性自然、委怀琴书的少年时代,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的生命转折,再至彻底归隐田园、以至晚年,勾画了柴桑古村落里美丽静谧的生长环境、“弱年逢家乏”的物质条件、儒学根柢的奠定、四仕四隐的原委,再现了陶潜不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个性,同时“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的雄豪健壮亦是其本色。尤其“唯《闲情》一赋”这一节,更是将少年(一说丧偶之后)渊明的细腻浪漫表现得奇妙华美,“秀出天外”。终身不废人事的靖节先生的深情于此可见。至于“逃禄的根源”,则以《感士不遇赋》为审视对象,指出“称情适性”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也是陶渊明一生所坚持的法则。
从桃花源到归去来
著者善于裁剪材料、巧妙布局。如“闲饮东窗”一节,将诗人关乎饮酒的诗句典故一并叙述,并统计其一百二十六首诗篇中与饮酒有关的文字,共九十多处。可以说,陶渊明“把酒大量地写入诗中,几乎篇篇诗中有酒,可谓有史以来第一人”。而在他《饮酒》组诗二十首中,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批判的诗篇几乎约占半数,说明陶渊明并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脱离尘世、超然物外、忘情现实。
尤其对陶渊明晚年的归结,以“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为题,首先描述的是著名的《桃花源记》:“就像一个迷路在沙漠之中干渴得要死的人,前望茫茫沙海,幻化出烟波浩渺的水面,饥饿与病痛也让陶渊明的眼前幻化出海市蜃楼,朦胧之中,他化作一位渔夫,划着一只小船,顺着一条桃林夹岸、落英缤纷的溪流,走进了一个梦幻的世外桃源。”这样的合理想象,对于体察诗人的心境、揭示精神的隐秘颇有助益。而檀道济的接济粱肉与渊明的“麾而去之”,更将病入膏肓的诗人的节操升华为具象。
全书最后三节“死如之何”“最后的牵念”“归去来兮”,可看做渊明临死前的三部曲,显示出他对死亡的达观、慨叹,对儿女们的骨肉深情。最后作者以一首《拟古九首(其五)》作结:“这位东方之士,神也?人也?陶渊明本人也。”他“清晨出庐,沿着一条青松相伴的山路,攀缘而上,直入山巅。山上白云缭绕,亭台楼阁,‘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这里没有寒冷,没有饥饿”,“那把断了弦的琴也在那里,只是琴弦早已修复。手把琴来,先弹奏幽怨的《别鹤操》,再弹高洁的《双凤离鸾》,激越又悠扬的琴声穿越天际,引来了成群的青鸾”。余音袅袅,回味不尽!
就是这样,作者以陶渊明大量的诗文本身作传记的资料,辅以相关史料,解释引申,翻译评论,以期获得对传主的全面认识。全书资料详实,取舍精当,不仅使人了解陶渊明本人的事迹,同时历史上的相关高人逸士、道德贤良亦在在多有。
著者虽云全书完全根据梁启超《陶渊明年谱》纪年纪事,但其间的发挥想象又是传记作者必备的素养。优美的语言与历史的熟稔应是优秀传记的重要条件。
元代赵孟頫《陶渊明像传》长卷刻本局部,此处呈现陶渊明手抚无弦琴和用头巾滤酒的典故。
“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
通过该书的“四观”,所谓以时观人、以人观人、以文观人、以境观人,我们的确可以对陶渊明有一个较为立体地了解,而不是简单的“田园诗人”的名号及浑身静穆、似乎缺乏情感交游的固有印象。“以‘六经’为主的儒家经典成了主导他一生的核心思想”,除了家族传承的基因,陶渊明人格节操的形成,“更重要的是饱读诗书的文化浸润”。
对于陶渊明的思想倾向,历来众说纷纭,聚讼不休,其实儒道两家在陶渊明身上得到很好的统一。早在1923年,开创近现代陶渊明研究的梁启超撰文《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提出陶渊明虽生长在玄学、佛学氛围中,其“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却都在儒学”,“他只是平平实实将儒家话身体力行”。梁启超称赞陶渊明是“真人”,其文艺是“真文艺”,并认为陶渊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两句话,真可为最合理的生活之准鹄“。他将”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作为渊明先生人格的总赞。
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人都有很好的启发,安贫乐道与随运任化本身就是无法截然划开的,没有对自然之”道“的领悟,是无法”安贫“的,也无法获得天人合一般的快乐,也不会搬柴运水、不避风日。儒家之道亦讲求顺应人情之”自然“,反对隔绝人世、绝情去欲。郭象讲”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便是对儒道两家的调和。在这个意义上,这本陶渊明”心灵游记“,对于我们今天思考生活的合理方式、生命的存在状态、真正的人的价值体现,都有适得其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