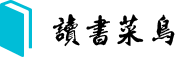作为一位20世纪举世闻名的文学巨匠,海明威的创作对美国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文学作品多涉及战争、斗牛、狩猎、捕鱼等题材。基于这些题材,他笔下人物大多是面对困难无所畏惧的“硬汉”形象,他们以惊人的毅力以及旺盛的精力,与困难对抗、搏斗,如《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五万块》中的杰克和《不服输的斗牛士》中的曼纽尔。海明威对男性力量的极致关注,让一些批评家认为他是一位患有“厌女症”的作家,认为其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大多是作为男性角色的陪衬与对立面存在的。
部分评论家从海明威的个人生活中找到所谓的证据,指出海明威对女性展现的是仇视与厌恶。优秀的作家一定是善于从生活汲取创作灵感的,但绝不会囿于生活。“我只知道我见过的东西”,海明威如是说。卡洛斯·贝克也提出:“他个人所做过的或所经历的并铭记在心的东西,就是他有兴趣讲述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他拒绝自由的虚构。”(《事物的本真》)但一味以海明威的生活和经历片面地分析其作品中的人物,尤其是那些女性角色,未免失之偏颇。
若对海明威的作品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不难发现,海明威在作品中展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并塑造了一系列复杂饱满的女性形象。例如,《雨里的猫》,以女性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展现了战后女性的觉醒以及觉醒后的迷茫。尽管仍有不少人主张以二分法将其笔下的女性角色划分为“天使”与“妖女”两类,可实际上他笔下的女性角色在性格上是复杂且多彩的。海明威真实地记录了女性的生活,反映了她们在现实中的挣扎与反抗。海明威并未打算简单地以“天使”或“妖女”这样的形象来表现女性,他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别有深意的。

一、故事梗概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围绕“猎狮”这一中心事件,以近一半篇幅的人物对话推动情节的发生并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虽然着墨较多的情节还包括猎杀野牛,但麦康伯“猎狮”时的软弱和退缩才是一切得以发生的初始原因,他的不堪令作为妻子的玛格丽特失望并与更具男性魅力的威尔逊发生性关系。妻子的背叛和刺激,自己的懊悔又让麦康伯在猎杀野牛时英勇无畏,可突如其来的变化让玛格丽特不安,并决定开枪,这才导致了最后的结果。海明威在描写情节时将多个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以一种序列式的结构串联起来,用张弛有度的节奏讲述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最后留下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开放式结局。
玛格丽特作为文中唯一的女性角色,又是“弑夫”案的中心人物,一直以来和《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海伦共同被当作“妖女”的典型。正如猎手威尔逊认为是玛格丽特趁机射杀丈夫一样,许多评论家都借他口中那句“干得真漂亮”将玛格丽特认定为真正的“谋杀者”。可玛格丽特是否真的是穷凶极恶的“弑夫”恶女,或许还应回到文本再次探寻。
二、玛格丽特的人物形象
(一)传统定位下的“妖女”
在认定玛格丽特是弑夫“淫妇”的评论家看来,玛格丽特同海明威笔下其他的“妖女”一样。她们凶悍势利、贪婪放荡、丧失道德、诱惑男人,对男人主体地位起破坏作用。她们的存在对男人的主体意识是一种直接的威胁,甚至极其恶毒地把男人置于死地。“小说从来不是孤立地处理人物性格的,人物的性格是和人物的行为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小说鉴赏》)评论家们往往从玛格丽特的所作所为中得出结论,并为其打上“妖女”标签,认定她危及男人的主体意识,使其再也抬不起头来,甚至恶毒地把麦康伯置于死地。
在“冰山原理”的指导下,海明威尤其擅长以“电报式”对话和简洁的描写,表达出直白辛辣的讽刺,或给读者透露出更多的信息。小说中玛格丽特同麦康伯的对话处处暗示了她的不屑。当威尔逊和麦康伯谈论第二天的狩猎时,玛格丽特用“可爱”来形容他们第一次的猎狮行动,更声称“如果把野兽的脑袋打得稀巴烂也是可爱的话”。可实际上,正是糟糕的狩猎让她对丈夫失望透顶。
文章开头十分耐人寻味,他们“都坐在餐厅帐篷绿色的门帘下,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对于喝什么的问题,玛格丽特否决了麦康伯的提议,反而选择了和威尔逊相同的酒。面对这样的场面,麦康伯并不气恼,还随声附和着。海明威用简短的四句对话就暗示读者一定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并迅速地展现出了人物关系,即麦康伯在妻子面前的唯唯诺诺。
玛格丽特是个美人,并善于利用自己的美貌。她曾靠美貌和社会地位赚取了五千美元的广告费,尽管“她从来没用过那些东西”。玛格丽特的美貌让麦康伯舍不得和她离婚,麦康伯的富有也同样让玛格丽特舍不得离开他。尽管麦康伯软弱怯懦,缺乏男子气概,玛格丽特更是频频出轨,但“他们的婚姻基础相当牢固”。这种交易式的婚姻在他人眼中成了“令人艳羡的、始终经得住考验的爱情”,这些字眼带着浓烈的嘲弄,并且随着情节的发展,这种讽刺越来越明显。
玛格丽特美丽迷人,也虚伪善变。因为对猎狮时惊慌失措的丈夫感到极度失望,但凡提及此事,玛格丽特便十分抗拒,甚至选择躲避。可再出现时,她就“精神抖擞、兴高采烈、楚楚动人”了,一边挑逗着威尔逊,一边又对丈夫甜言蜜语起来。她的行为将“妖女”的蛊惑、虚伪表现得淋漓尽致。威尔逊得出了结论:“她们果真十分冷酷,威尔逊在心里想:最冷酷的人总是如此迷人与具有侵略性;她们一旦变得冷酷,她们的男人都得受罪,要不就是精神崩溃。”
玛格丽特偷情被麦康伯撞破时二人的对话或许的确会让人觉得她就是一个无情的荡妇。就像菲德勒在《论海明威小说中的爱情描写》中将其定义为“十分忧伤和失望的荡妇”,并认为正是因为麦康伯离间她与威尔逊之间的感情才会被其杀害那样。当麦康伯为妻子出轨气急败坏时,玛格丽特却毫不避讳。面对麦康伯“你去哪儿了”的多次质问,她都并未正面回答。麦康伯怒斥与辱骂她时,玛格丽特才正面回击道:“那你就是个孬种。”这里的标点符号似乎比对话内容的表现力更强。麦康伯的话都是以问号或感叹号结尾,而玛格丽特的话大多是以句号结尾,她的情感就连在攻击丈夫是“孬种”时也一样毫无起伏。似乎玛格丽特认为,她的不忠并不是一件罪恶的事,一切都是因为丈夫过于懦弱不堪。彻底撕破脸后的玛格丽特也并不在意这件事。她甚至还能淡定地用撒娇的语气和“别怪我不理你”的威胁让麦康伯不要打扰自己睡觉。海明威的反讽艺术再一次发挥了精彩的作用,玛格丽特在对峙期间一直称呼麦康伯“亲爱的”,在这样的情景中,多次出现该称呼格外引人注目。玛格丽特表面上的温柔甜蜜和实际上的嫌弃与背叛形成鲜明对比,不断地刺激着麦康伯的神经,让他崩溃抓狂。
(二)对玛格丽特的重新审视
1.没有杀人动机的“谋杀犯”
对玛格丽特是“谋杀者”的指控一直长盛不衰,可她真的是一个罪孽深重的“杀人犯”吗?海明威并未直接点明,而是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如果回到“案件”本身寻找答案,玛格丽特似乎并没有足够的“杀人动机”。一方面,在和麦康伯的婚姻中,玛格丽特是占据上风的;另一方面,海明威早就借猎手威尔逊的话告诉我们“她不蠢”。如果她想让懦弱的丈夫失去他可怜的生命,只需要冷眼旁观就好了。即便玛格丽特不开枪,在野牛的攻击下,麦康伯也凶多吉少。玛格丽特完全没必要多此一举,更何况她的行为一定会引起怀疑。玛格丽特和麦康伯的婚姻虽然是金钱与财富的交易,但的确是相对稳固的。虽然在结婚十一年后,玛格丽特的美貌开始走了“下坡路”。海明威借第三人称叙述者对玛格丽特现在的容貌进行了客观评价,“曾经”“现在”“在非洲”“在家”,时间点和地点的交错点明了玛格丽特目前尴尬的处境,但是她的丈夫并未因此离开她。所以,尽管这段婚姻充满了嘲讽意味,但玛格丽特不会随意改变这一现状,她没有足够的杀人动机。
2.敢于反叛的“新女性”
玛格丽特的确不是海明威笔下的“天使”,但也绝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坏女人。她的形象是复杂的,是值得令人深思的。可以说,玛格丽特是一个追求自由的“新女性”,她打破了传统的道德束缚,敢于自由追求喜欢的男性,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当然这并不是为她开脱,至少总体来看,玛格丽特是一个坦率的,敢于反叛的女性。比起小说中的两位男性来说,玛格丽特似乎更能正视现实。猎狮结束回到营地后,麦康伯和威尔逊就把之前的事抛在脑后了。环境在故事中有很多作用,可以形成气氛、增加意蕴、塑造人物形象乃至建构故事。海明威很善于通过环境表现氛围和人物的心理。麦康伯在帐篷外坐下,“微风轻拂,绿荫斑驳”,这样的环境是轻松惬意的,也暗示麦康伯窘迫暂时还没被捅破,他是放松的。威尔逊说着:“你打到狮子了,而且,还是头超棒的狮子。”麦康伯也回应道:“很棒的狮子,对不对?”这里玛格丽特的反应很奇怪,“她望望这个,再瞅瞅那个,仿佛这两个男人她以前从来没见过似的”。如果威尔逊她不熟悉或许还说得过去,但自己的丈夫怎么会不认识呢?她自然是认识的,不仅认识,还深知丈夫的特性。通过文中后面的内容,不难发现,这两位男士的对话讽刺意味十足。自己的懦弱没被发现时,麦康伯自然是舒适安逸的,威尔逊不断吹捧着。可见麦康伯的懦弱胆怯、逃避以及男人们之间的虚伪。而玛格丽特却能为这样的行为感到羞耻难堪。当她目睹了麦康伯的无能与懦弱时,她选择了多次和威尔逊调情,甚至用偷情的方式表达内心不满。尽管这种行为并不道德,但玛格丽特内心的愤怒与失望似乎只能通过这样的形式展现出来。甚至可以说,她是希望用这样决绝的方式激起丈夫找到属于男性的力量与胆识。
3.悲剧角色玛格丽特
从另一个角度看,玛格丽特身上还带有鲜明的悲剧色彩。丈夫的软弱无能令她失望而痛苦,她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婚姻不过是一场金钱与美色的交易。这种清醒中的痛苦让她选择了用出轨的方式对待丈夫,尽管人们因此定义其为“妖女”。她追求男性的力量,选择和威尔逊偷情,但在威尔逊眼中,她不过是众多狩猎艳遇之一,是一个卑鄙的女人。当麦康伯死于枪击后,威尔逊更咬定是玛格丽特蓄意谋杀。玛格丽特从始至终都没能得到一个真正以平等态度对待她、尊重她的男人。人们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玛格丽特是否故意杀害了麦康伯?从动机来讲,玛格丽特的“弑夫”并不成立。但她为何要开枪?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海明威在创作时总是用重复的方法来告诉读者隐藏的信息。当玛格丽特看到麦康伯突如其来的勇猛时,她连说了三个“我讨厌这次追猎”。为何丈夫不软弱了,玛格丽特却并不高兴?当麦康伯炫耀自己的英勇无畏时,玛格丽特虽然一如既往讽刺着“你突然彪悍起来了!彪悍得不得了!突然不得了了!”但这里的重复和三个明显的感叹号,无一不在表明她的不安与恐惧。她恐惧的是自己和麦康伯原有的平衡就要这样被打破了,所以她讨厌这次追猎,她不断用嘲讽的方式掩盖内心的不安。因此,她举起了枪。或许她想的是如果自己击杀了野牛,那么她和麦康伯那种平衡的关系就能维持下去,甚至救了麦康伯的性命,她的地位就更稳固了。这样急切地想维持自己地位的想法促使玛格丽特开了枪。但是她没有击中野牛,而是击中了麦康伯。当威尔逊用淡漠的语气说“干得真漂亮”时,玛格丽特一直重复“别说了”,在重复的背后,是她的懊悔和痛苦,她反叛的冲动促使她成了“凶手”。她不仅要承受“弑夫”的罪名,还要一直活在懊悔的痛苦之中。因此,海明威在玛格丽特身上呈现了女性的痛苦挣扎,其中包含了他对女性的关注与同情。玛格丽特不应是一个被简单定义的“妖女”,她有令人反感的地方,但同时她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生动饱满的女性形象。
三、海明威笔下的其他女性形象
在其他作品中,海明威也创作出了性格各异,复杂的、引人深思的女性形象。海明威对这些女性的描写,深刻地反映出他对女性生存状态的体察,同时也说明,海明威是一位能站在女性角度反映男性和社会问题的作家。他观察并思考两性关系的不同状态,通过对话和极精准的动词来展现人物的心理,试图以笔下女性形象性格的塑造,表达对女性的同情与担忧,关注女性的生存和精神世界。
在《雨中的猫》中,海明威一改往日对男性力量的关注与渲染,将女性角色作为第一主角,通过环境和众多意象,塑造了一个迷茫孤寂、散发着忧伤气息的女性形象。他将故事背景置于异国他乡:滂沱的雨水、肃穆的战争纪念碑、空荡的广场,整体灰暗的色调给读者带来了压抑感,奠定了暗淡、忧伤的感情基调,更暗示了女主人公迷茫、彷徨、孤寂的心理状态。本是一同出游的夫妻却并没有太多交流。面对妻子的种种诉求,男子敷衍几句就作罢,二人之间透露着一股不属于爱人的疏离感。或许正是因为自己的迷茫与无助,才会让她对“雨中的猫”产生一种同情,一种强烈的欲望。女主人公不断地提出自己的诉求,将内心积压已久的愿望强烈地表达出来,这是女性意识的觉醒。然而丈夫不但不理会,还让她闭嘴。这种不平等的男女关系,被漠视的状态再一次让女主人公失望、迷茫,甚至痛苦。
海明威关注到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对女性给予充分关注。在他的笔下,女性角色性格多样,特色鲜明。那些被单纯归于“男性附属”的女性或更邪恶的“妖女”有着更复杂的性格特点。长期居于男性压制下的女性们不断地觉醒,她们开始渴望得到他人的关注,并赋予自己的思考与主见。《雨中的猫》的女主人公对“猫”的渴望与救助是自我渴望获得关注的投射,《白象似的群山》中吉格对男主人公的花言巧语提出反驳,通过语言交锋展现心理上的较量,也表明了她的觉醒。
无论是《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里的玛格丽特,还是《雨中的猫》里的女主人公,再或者《白象似的群山》里的吉格,她们性格各异,有不同的背景和经历,但都象征着女性的反抗与觉醒。这也正说明海明威绝不是一个狭隘的“男权主义”作家,恰恰相反,海明威能以独特的角度,细致地观察两性关系的多样形态,展现女性的处境和生存状态。因此,对于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形象,我们应该投以更客观积极的态度,从更丰富的角度进行解读。